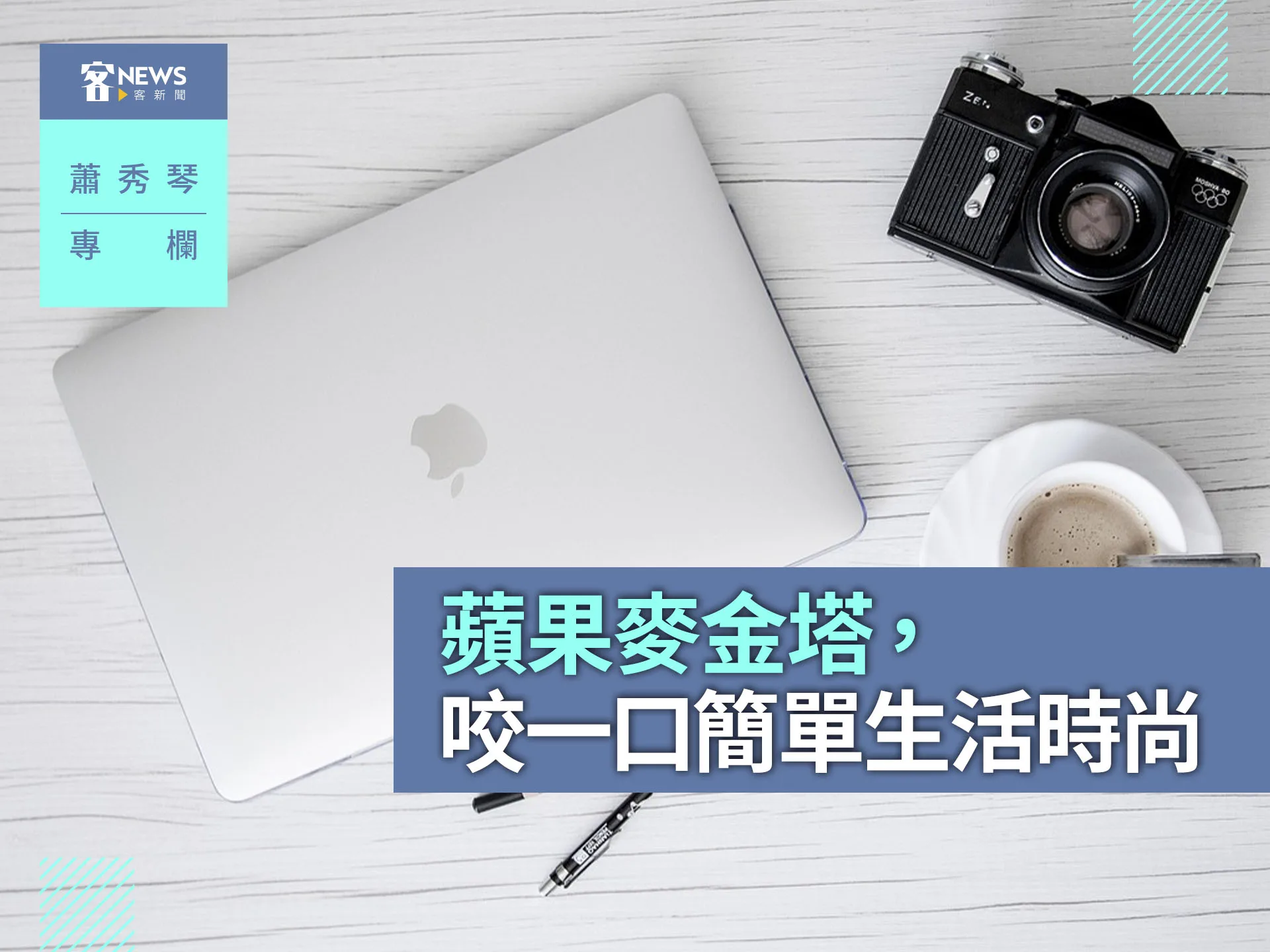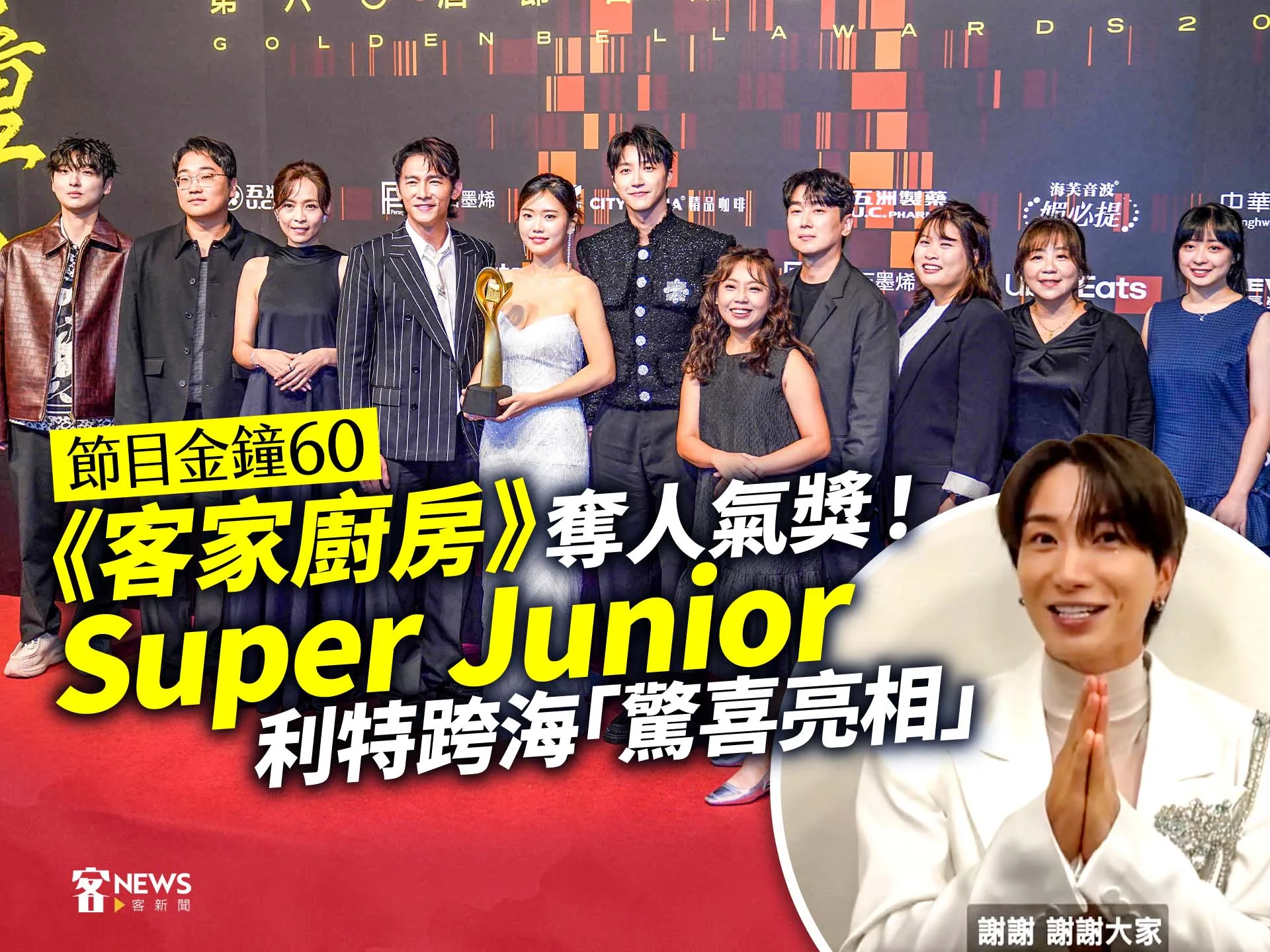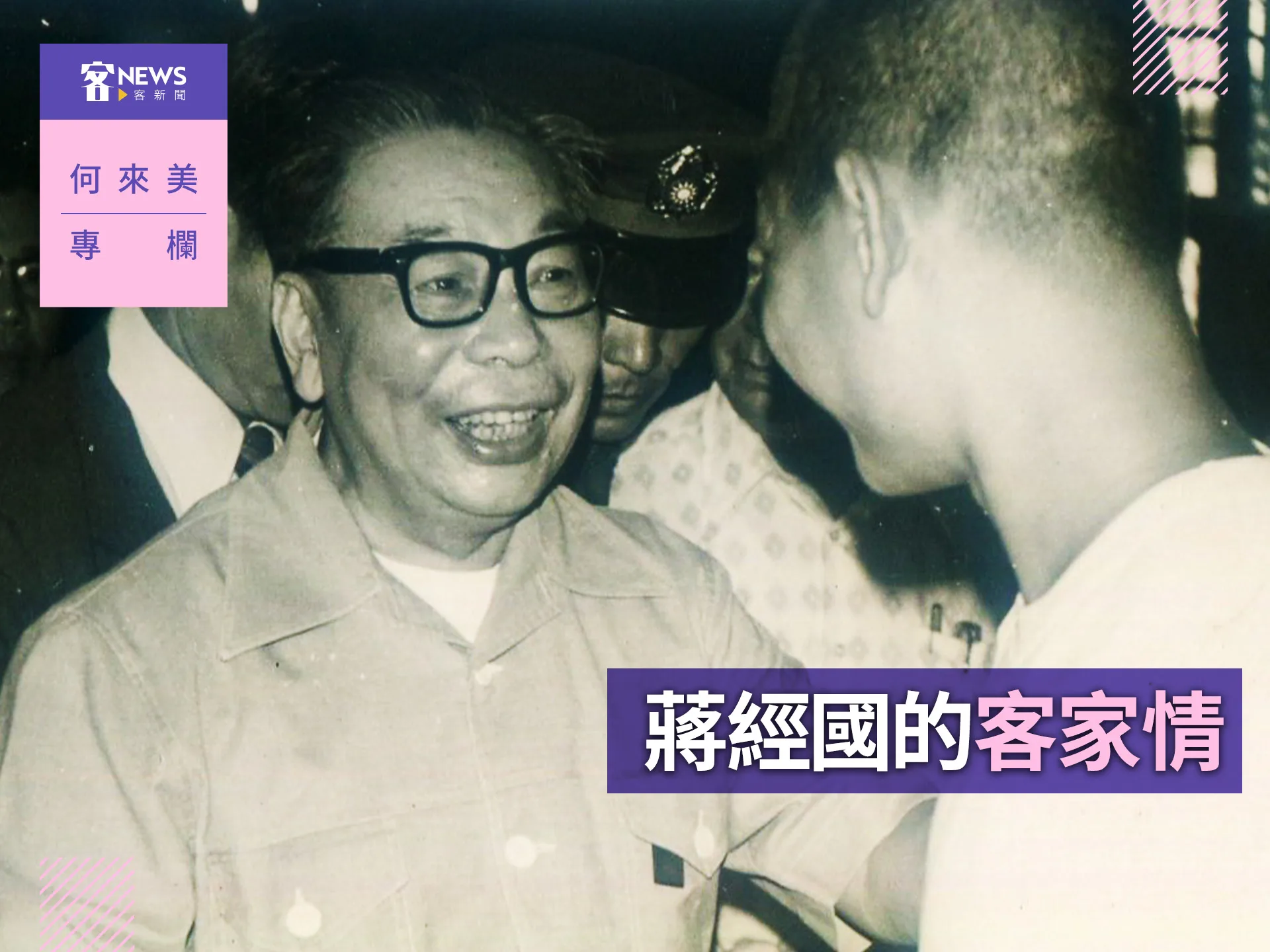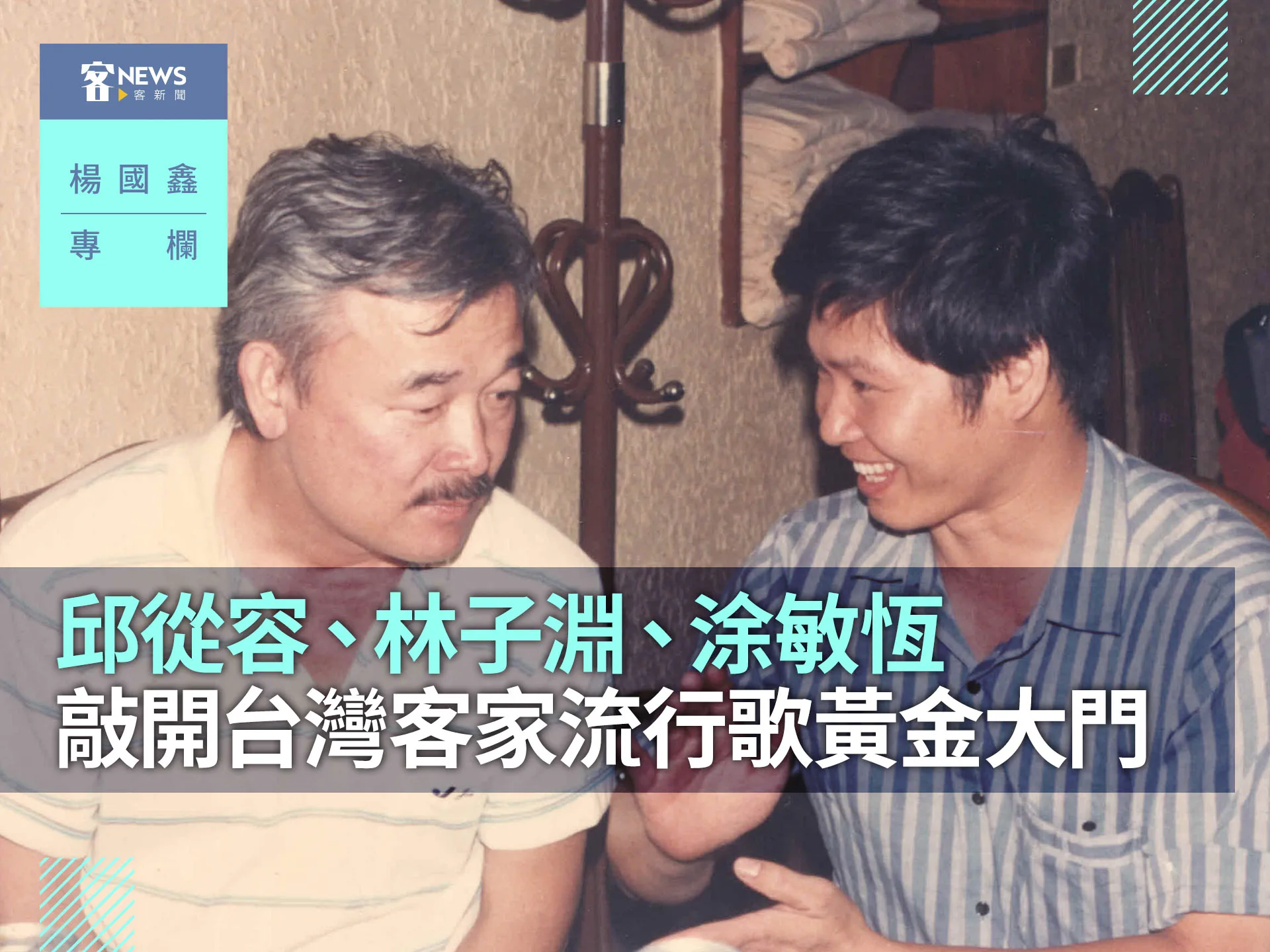文/蕭秀琴
曾任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作家暨譯者,著有《料裡風土:往山裡去的地方,九種食材從山到海建構客家飲食》、《料理臺灣:從現代性到在地化,澎湃百年的一桌好菜》等書籍。現居離台北城約一個小時的小鎮,持續文字工作。
在我們的島,這種物候短暫一瞬,轉眼就日烈晟目,讓葉子轉成了深綠,使新發的筍上笐(shongˋ gong,海陸腔)為枝,香椿芽嫩心成梗。若葉是嫩葉,日文漢字わかば(wakaba)是初夏寄語,明治詩人正岡子規愛以此作俳句,「午後的微風吹得新葉閃閃發亮」,此時台灣島上的風還涼涼的,從四方海上交融吹送而來。
薰風若葉詩性的季節,文學性的描述必不可缺,若葉風飄、若葉雨露、若葉雲谷到若葉櫻餅,詩人用俳句、短歌和詩文歌頌若葉生機勃發,台三線上只一座棚架就能包含全部,西洋瓜心、番瓜花和瓠仔頂……棚架上毛茸茸的若葉,迎著初夏微光向上伸展,承受春雨已歇梅雨未至不大不小風吹雨打。
台灣人的蔬菜在冬季盛產期滿載直到春天,即將步入夏季時節,五月的風不寒不熱正舒爽,小小的遺憾唯瓜果尚未大爆發,季節未到無法大快朵頤,一不留神就忘卻嫩芽新抽,獨獨客家人在當下偷得流光。
若要問西洋瓜心是什麼,得先弄清楚何以叫西洋瓜,阿婆也不清楚只得回,跟阿公的寶貝西洋鐘差不多一個意思,凡是跟著大航海時代而來的中南美洲物種,客家人不是以番就是用西洋作為前綴詞,一筆帶過。
客家人的西洋瓜一年吃個一兩次就覺得夠了有吃就好,果形不好削皮便罷,果尾有刺札人,皮破了黏液流出來想抓牢削皮都不容易,卻仍要大費周章地搭棚架讓藤攀爬,不就為了此際新綠的嫩葉嫩心嗎?在兩大豐盛之間,在名物消逝與登場的間隙,獲得一嚐私房菜的小小歡愉。


西洋瓜心愈簡單愈好吃,少許油鹽蒜頭爆香,下鍋快炒,起鍋淋幾滴米酒,盛盤。客家人不會說龍鬚菜,也不講佛手瓜更說不出隼人瓜,1930年代才傳進台灣也不受重視,只有客家人一年吃個幾次西洋瓜心,嚐一嚐初夏新綠。
植物新芽惹人愛,是因為看起來嬌嫩脆弱需要被呵護,西洋瓜心是佛手瓜的新生的嫩葉,一般稱為龍鬚菜,摘採七八公分的嫩株有五六片葉子和捲曲的莖,莖有人吃有人不要挑去。
客家人的初夏若葉最為人稱道是蕨仔,蕨本就是潮濕陰涼處叢生的植物,台三線的蕨可和美濃的水蓮拚比,都曾是野生遍地卻種植不易的水生植物,堪堪拿來做私房料理,旬味可食。
再來就是蕃薯葉了,這一味是母親的鄉愁,沒有媽媽不視它做健康的代名詞,常聽到春夏交替,風時不好,多吃全能蔬菜蕃薯葉可以幫助消化補充葉綠素,我的腦海卻飄來,不是說這叫豬菜嗎,或許能把豬養得肥肥的豬菜記憶,連結了吃了會健康的意念。
眼看一座瓜棚嫩蔓就好似滿眼盛夏果實,熟稔的耕作者不需要熟讀種植知識也能懂疏果的道理,摘掉莖葉茂密讓日光透進來,繁花似錦雖美卻會互相排擠生存條件,番瓜花摘掉一些烰菜妝點餐盤也美,吃花食心摘若葉,最極致的一道不過香椿芽拌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