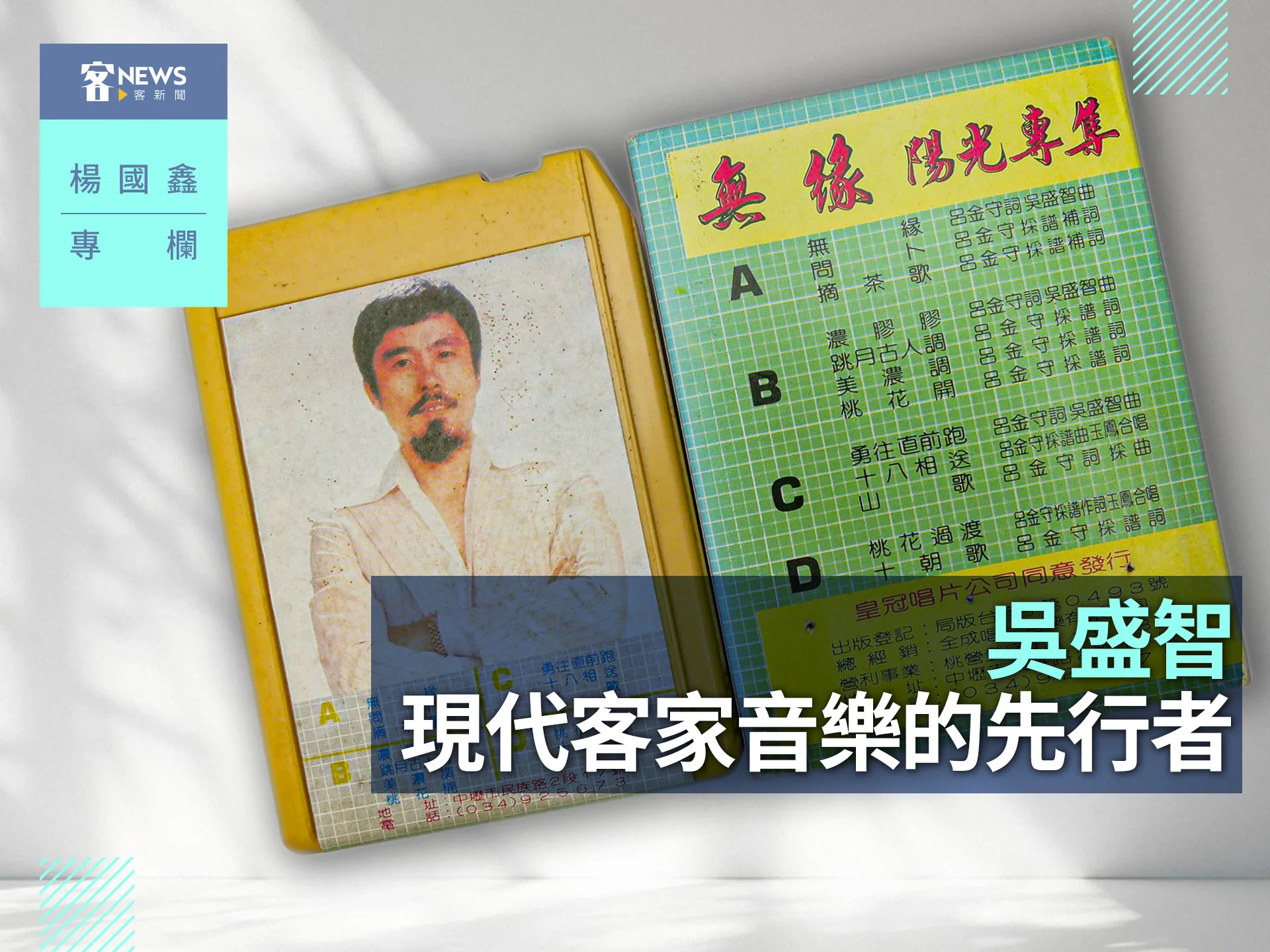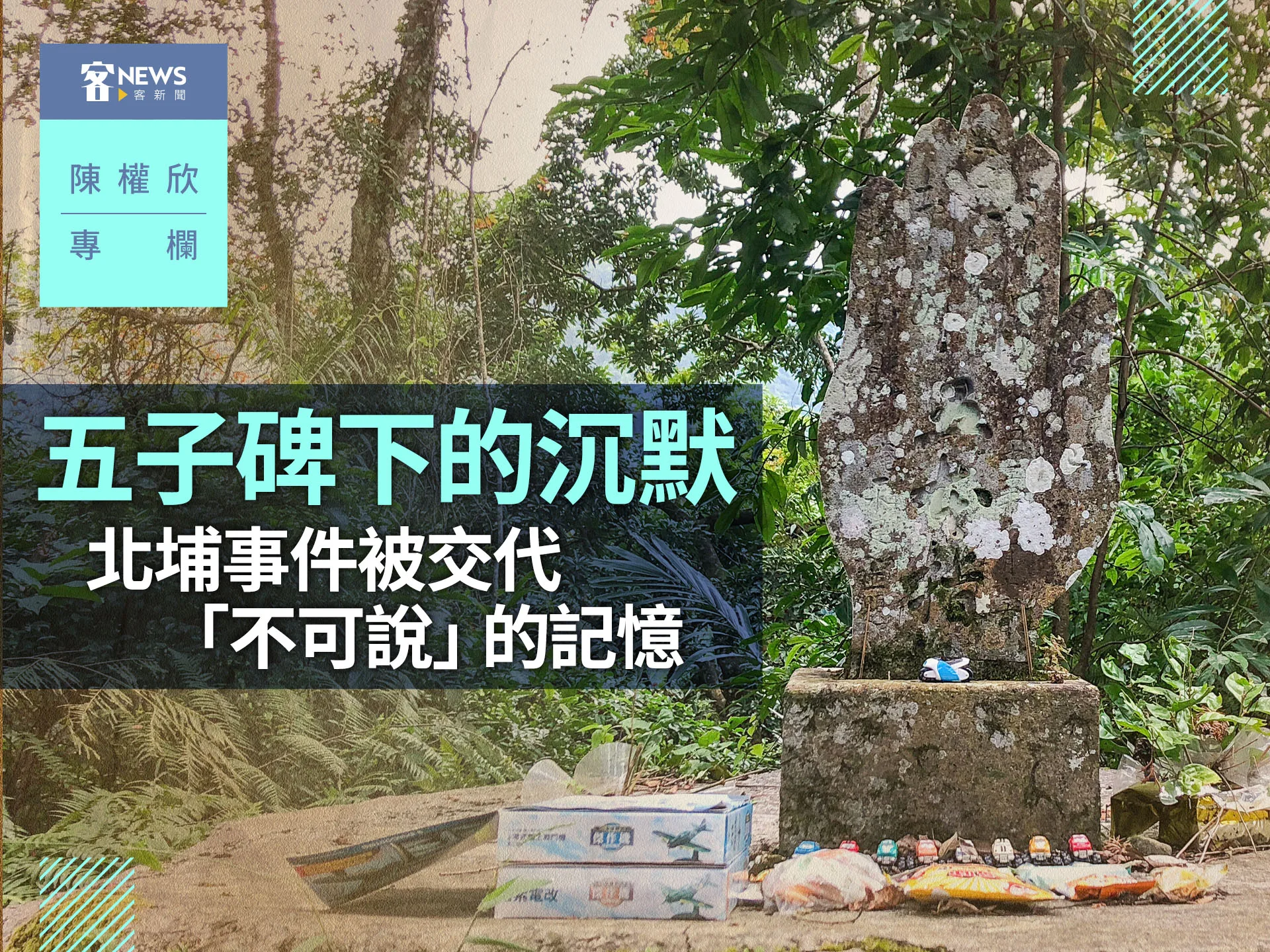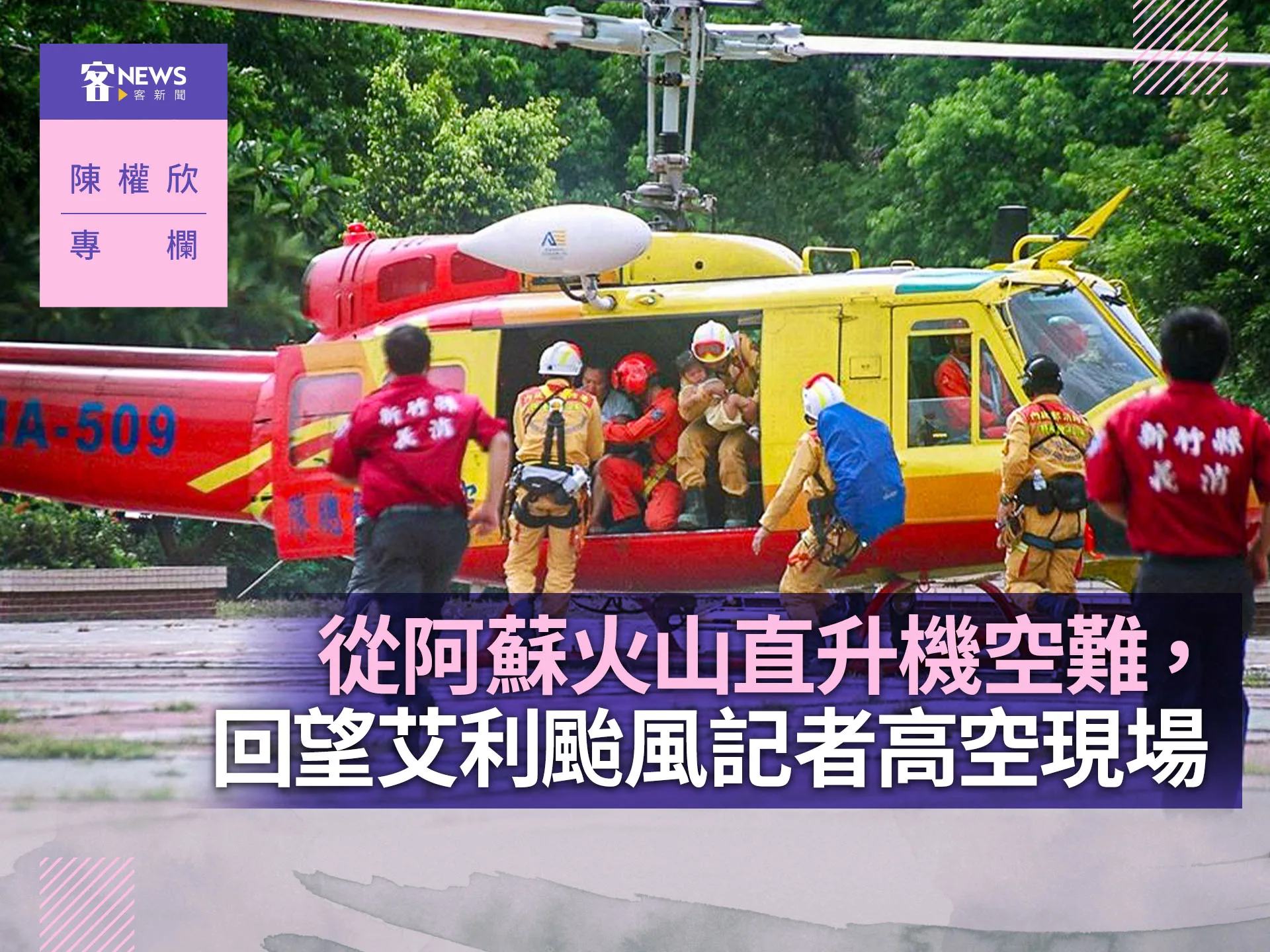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的缺點是「好為人師」。
哈佛大學近日拒絕美國聯邦政府的政治干預,成為震撼高等教育體系的關鍵事件。自哥倫比亞大學開出第一槍後,聯邦政府進一步擴張審查目標。普林斯頓大學、西北大學、康乃爾大學等校被分別凍結2至9億美元研究經費,甚至連尚未「違規」的校方也開始預防性自我審查。
這種政治壓力下的大學治理挑戰,與極右翼文化戰爭密切相關。正如極右翼保守派運動人士魯弗(Christopher Rufo)所說,目的是透過行政手段來「馴化」大學,使其遠離社會運動與進步意識形態,轉為中性、甚至保守的場域。魯弗甚至直言:「要讓他們屈服,不是因為你說服了他們,而是讓他們不敢再出聲。」
這場美國極右翼政治勢力對菁英大學的意識形態攻擊,影響的不僅是人文學科,也擴及其他領域的科學研究。聯邦政府在2025年初宣布削減科研費用、限制簽證核發並審查海外資金來源,使得自然與生命科學也陷入某種「寒蟬效應」。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批評這是「殺雞取卵」策略,可能毀掉美國菁英大學享有的全球頂尖地位。
最具象徵意義的反應,來自傑森·史坦利(Jason Stanley)教授,他是任教於耶魯大學的哲學教授,也是研究極權主義的學術權威。他在最近接受美國公共電視訪問時表示,美國大學正陷入與納粹時期德國學界類似的命運,當年教授們因自保而沉默,最終讓知識體制變成政權宣傳機器。因此,他選擇從耶魯大學辭職、轉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職,乃是出於對美國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狀況惡化的失望。他說:「當政府干預學術內容,而校方選擇保持沉默,那就不再是真正的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賈費(Jameel Jaffer)指出,美國聯邦政府不應將《民權法》第六章直接轉化為行政懲罰工具,其應用必須經由調查、程序與比例原則。他援引過去司法判例,提醒大學不只是受聯邦政府補助的機構,更是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思想實驗室。
但多數大學校方擔憂訴訟曠日廢時、人才流失、學生與家長撤資等風險,不敢與聯邦政府正面衝突。例如,加州大學默默撤除「多元聲明」政策、密西根大學關閉多元、公平與共融(DEI)機構等做法,形同屈服於聯邦政府的政治干預。
根據2025年蓋洛普調查,美國民眾對高等教育的信任度降至歷史新低。僅36%表示高度信任,其中共和黨支持者比例更低至20%。而對學術自由感到關切者,大多集中於少數知識圈。這樣的社會氛圍,導致聯邦政府肆無忌憚地整肅菁英大學。
此刻,我們該問的不是「川普可以這樣做嗎」,而是「如果所有人都不說話,誰來保護我們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