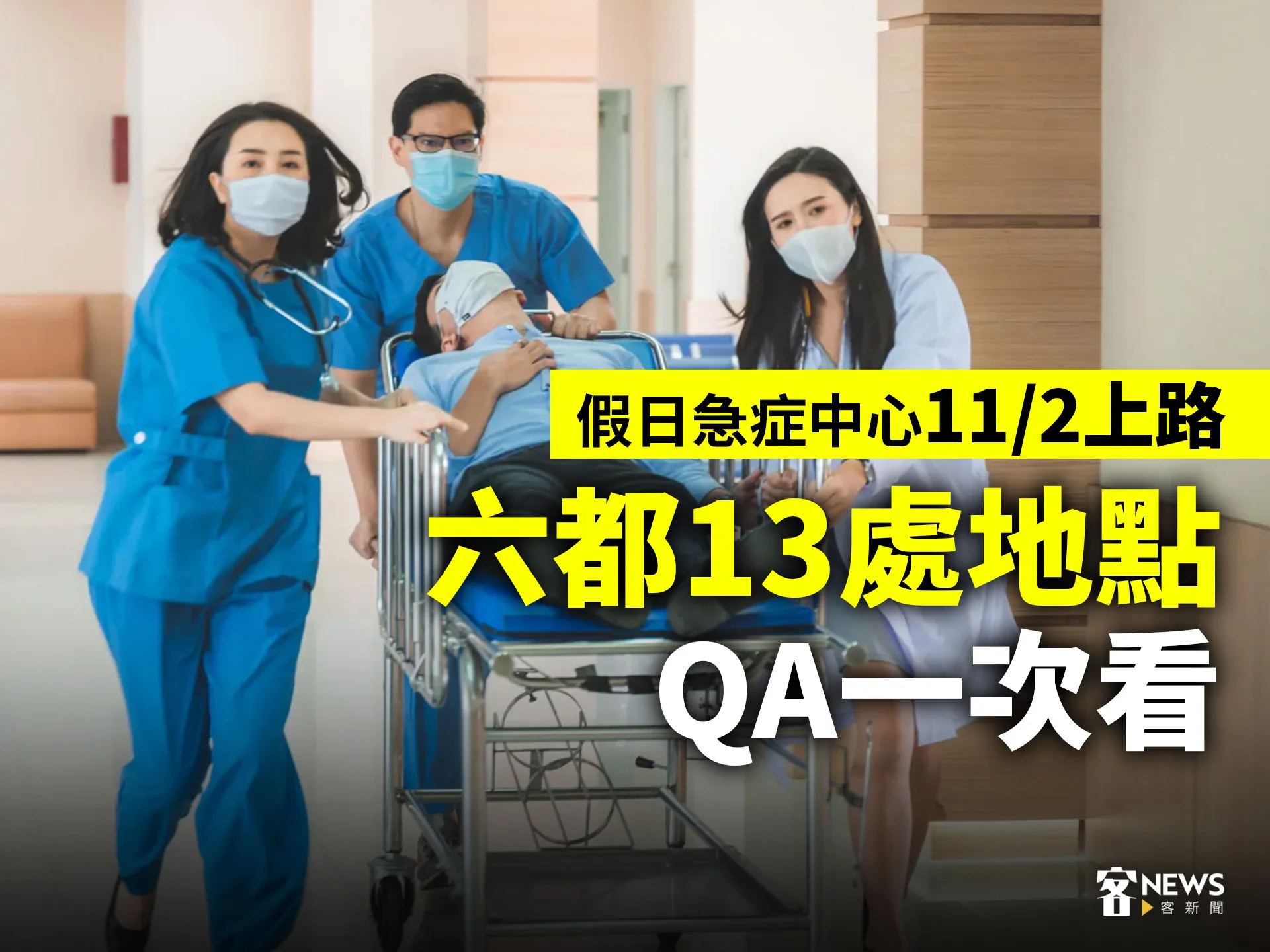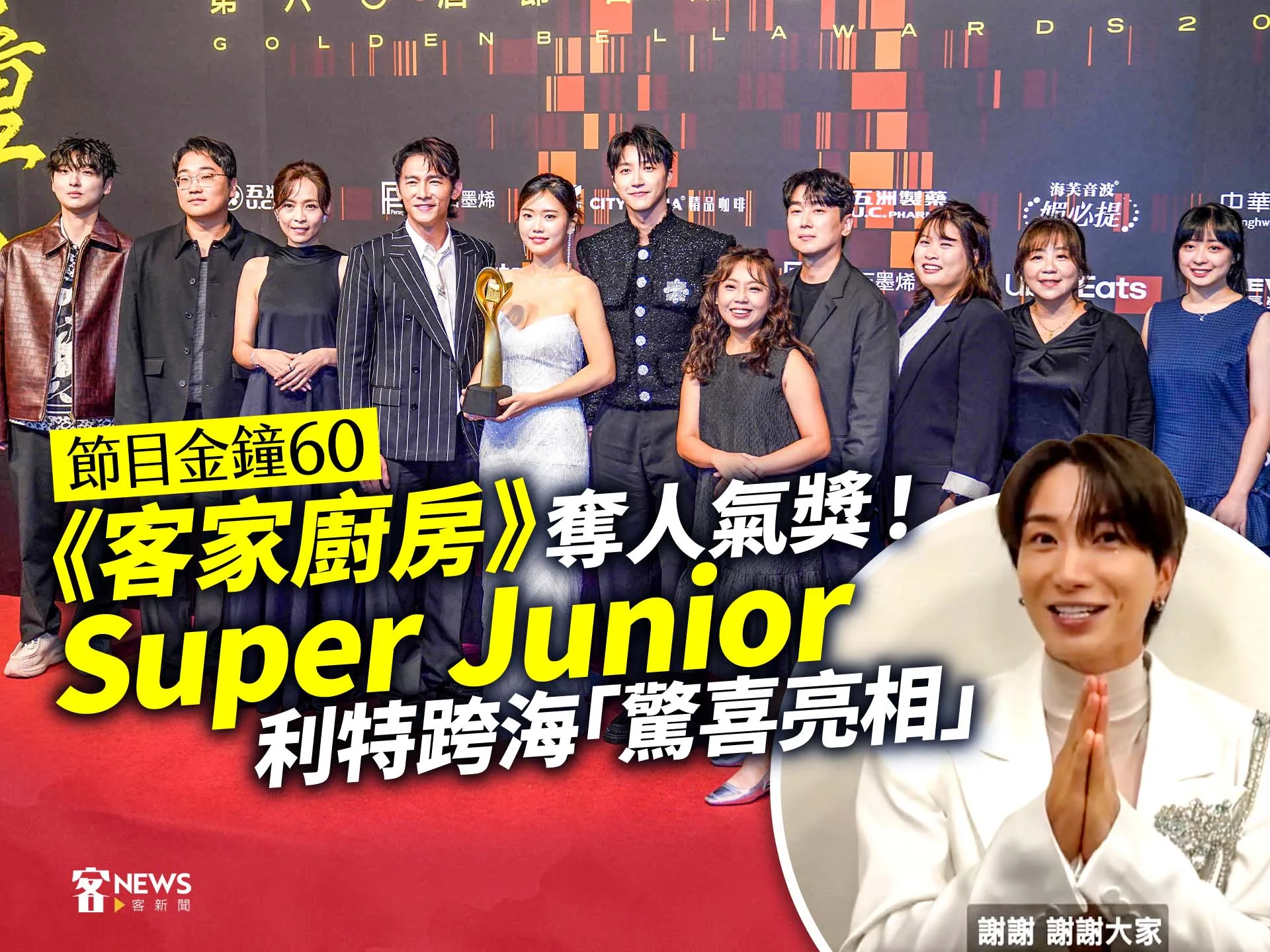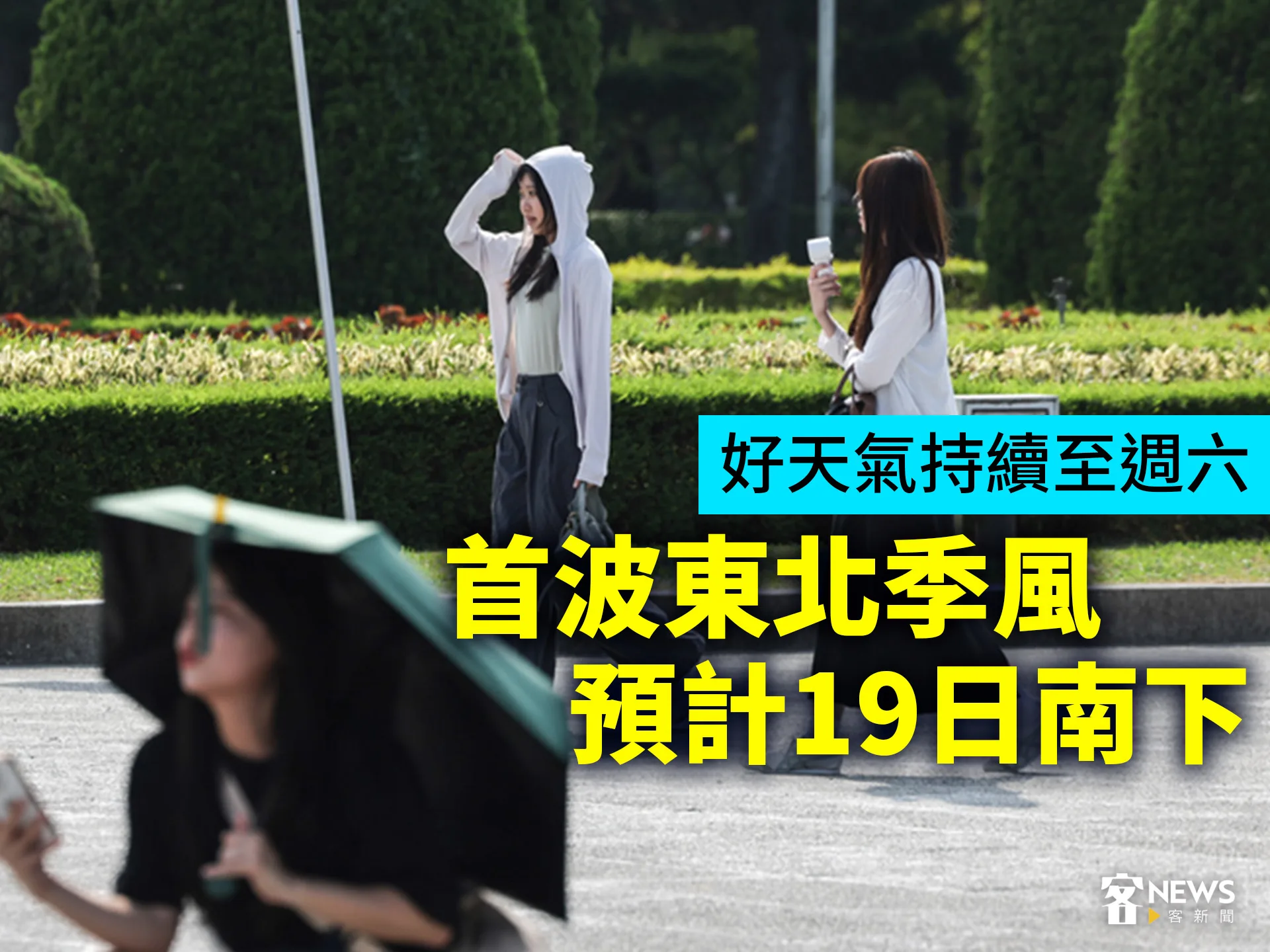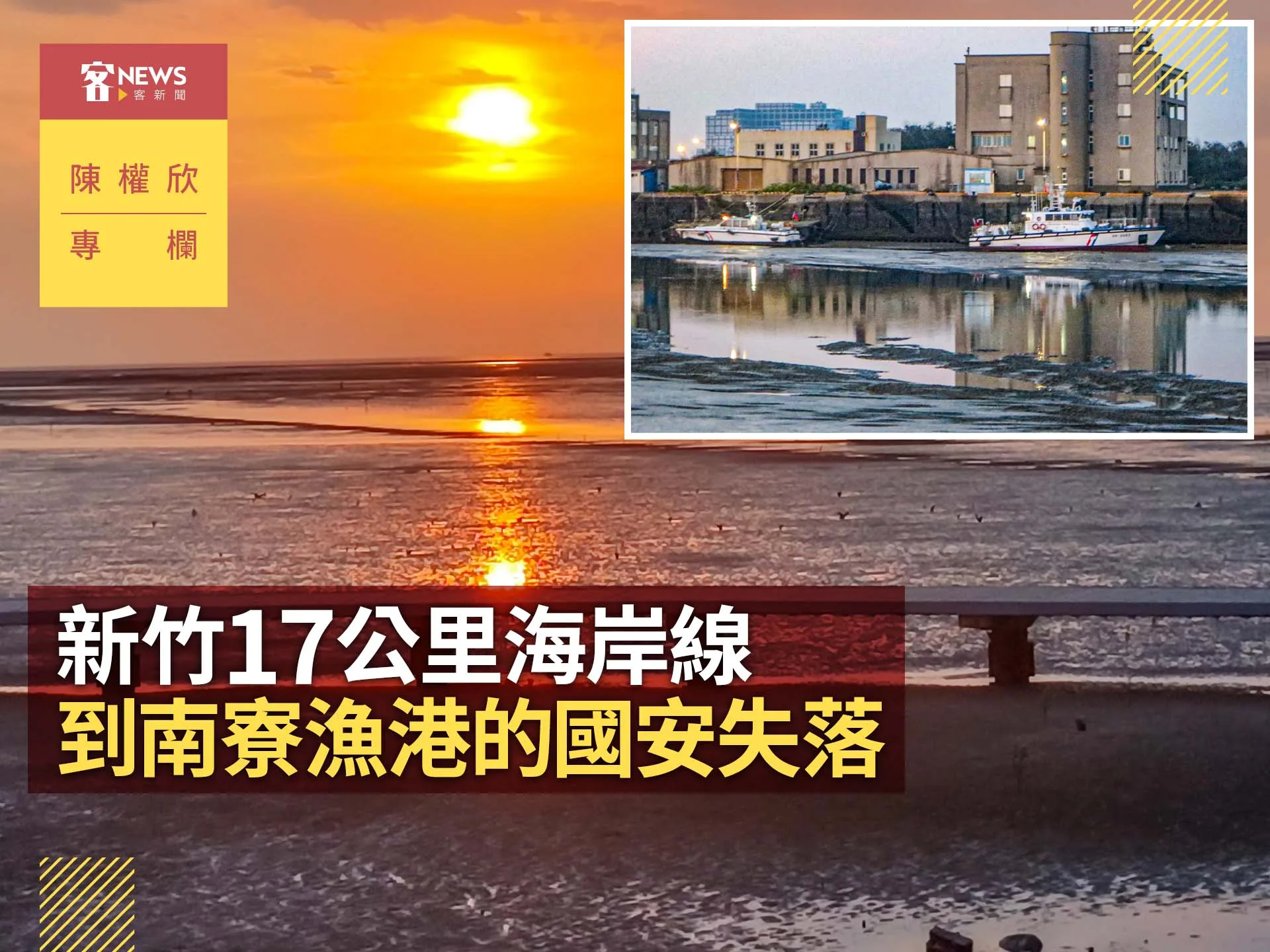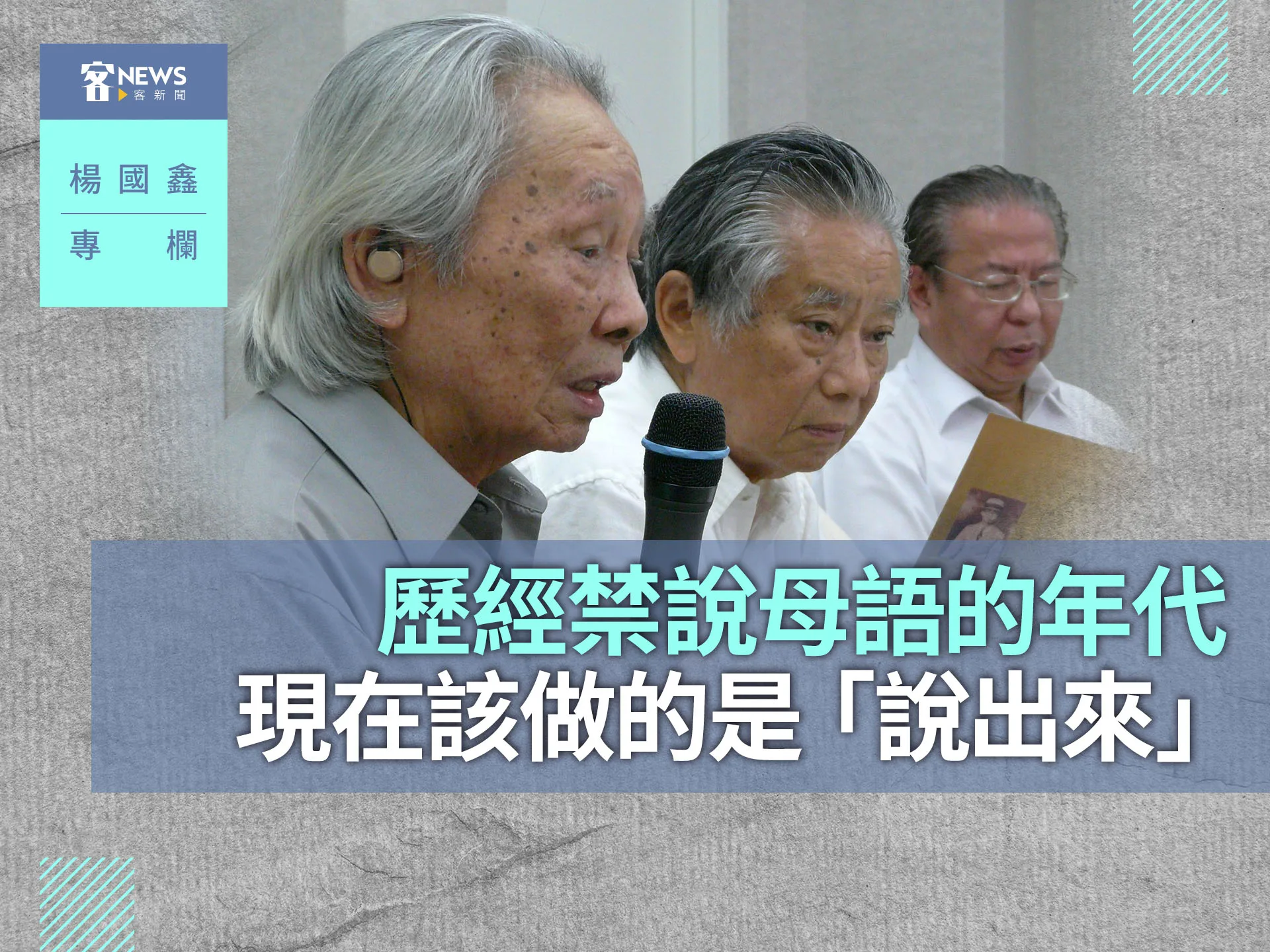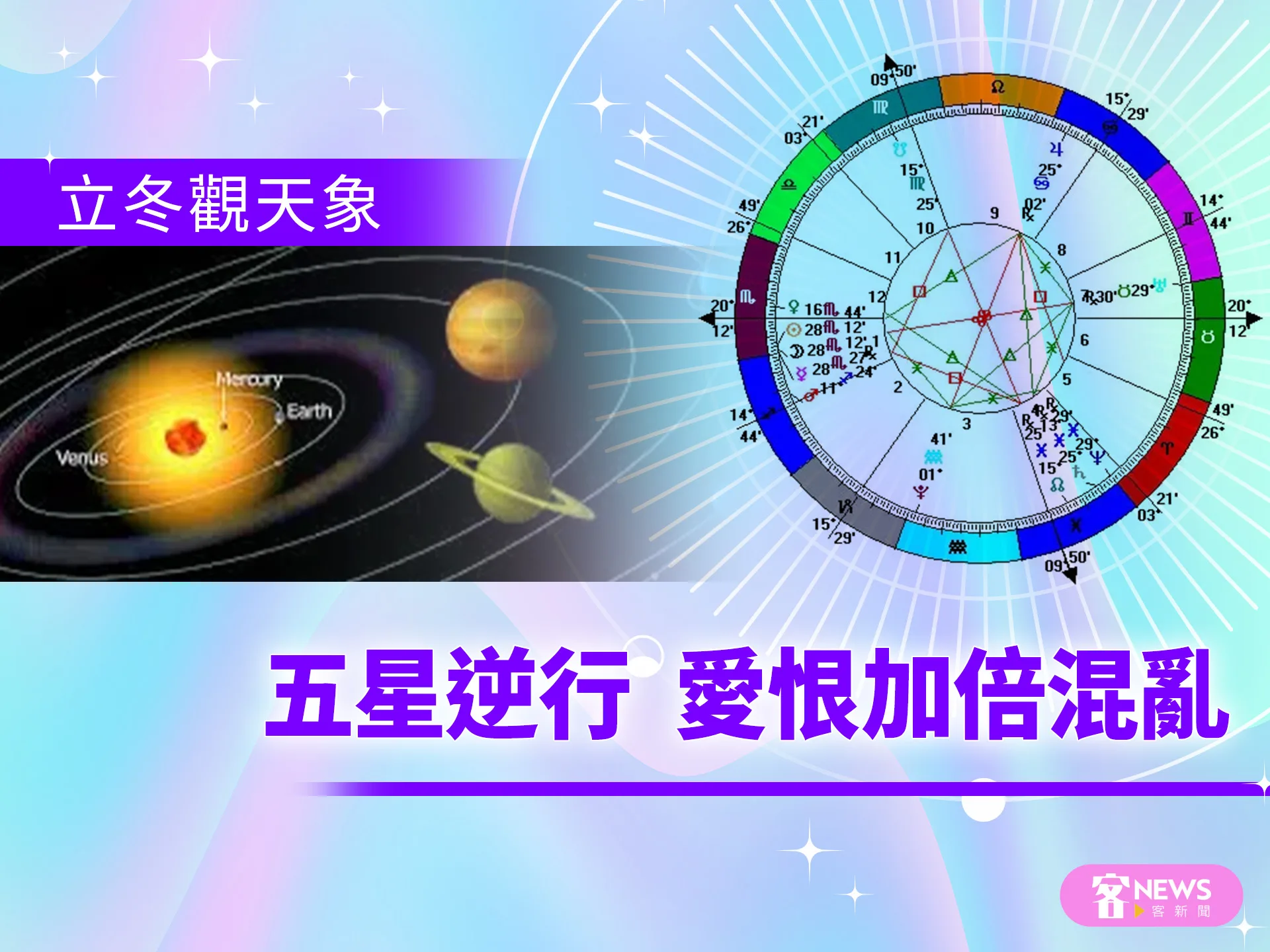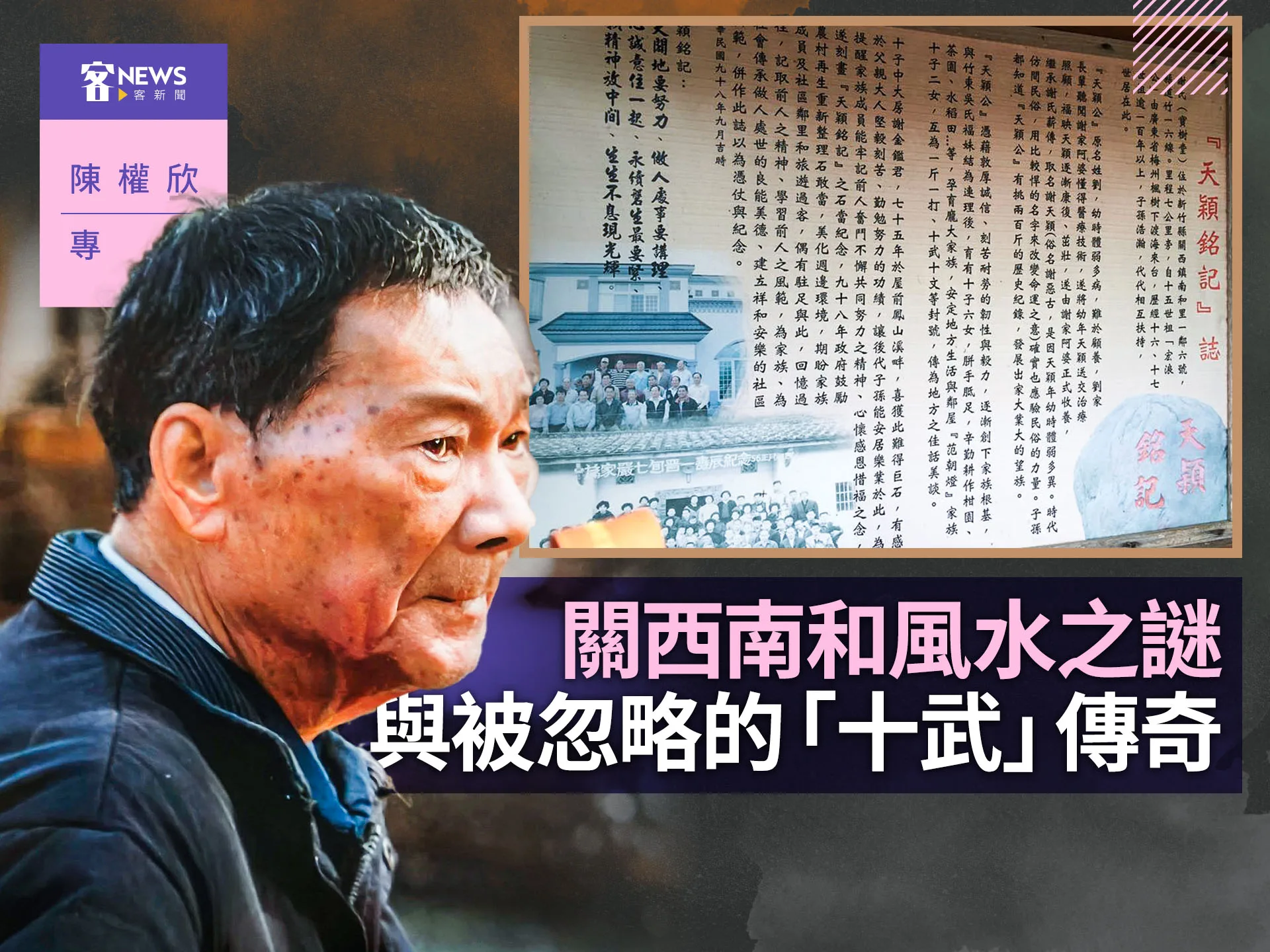文/蕭秀琴
曾任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作家暨譯者,著有《料裡風土:往山裡去的地方,九種食材從山到海建構客家飲食》、《料理臺灣:從現代性到在地化,澎湃百年的一桌好菜》等書籍。現居離台北城約一個小時的小鎮,持續文字工作。
1934年畫家李梅樹以《切番薯之女》參加第八屆臺展並為總督府購藏;那幅畫是穿著一襲粉色大襟衫的女人,坐在井邊低著頭專注眼前的工作,右手拿傳統菜刀左手拖著番薯,腳邊還有一大籃未切的番薯,看起來使用的工具是要切番薯的刀,但以現在人的廚藝看,切菜不用砧板也太厲害了,不怕切到手嗎?我媽說;現在的女孩子哪裡知道,切番薯是下一刀,刀子一拐,就下來了;畫家果然觀察細微,誠不欺我。
事實上,這幅畫讓人感到驚訝的還不止如此,專注眼前的女人背後遠山如畫,優雅得不像是在勞動,當然,李梅樹的女人一向時髦秀氣,即使是勞動中的婦女都不忘打扮,像是,1942年的《麗日》是黃昏時刻,一群穿著洋裝正準備回家的女孩,其中提著一籃子番薯的女孩子穿著繡花領的襯衫和兩片裙,更知名的一幅是1948年的《黃昏》,取法布列東1859年《召回拾穗者》的構圖,但主題是在番薯田裡撿番薯,從老到少的六個女人都穿著長長的百摺裙。
這些形塑台灣女人印象的畫作,以番薯為標記實在是貼切不過,番薯在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幾乎無處不在,更寫實一點,看楊英風的版畫《嬉》,這是1959年他在《豐年半月刊》時期的農村作品,佔了畫面一半以上的毛籣(mo‵ lam 海陸 ,圓形竹籃子)和番薯葉,以及穿著旗袍蹲著處理番薯葉的雙手,比起左上角兩隻可愛的小豬所佔的畫面還要大得多,料理豬菜(番薯葉)餵豬是嬉戲是趣味更是希望,似乎台灣人有了番薯就有了未來。
我想沒有人可以否認這個觀點,早在十八世紀初期的《六十七兩采風圖》中的圖說有,「番薯又名地瓜,蔓生結寔,于土皮有紅、白二色,生熟皆可食,亦可研粉,土人用以燒酒。其種出文來國,臺地栽甚廣,民番藉食,誠為歲歉之一助也。」把番薯當作飯,補充米糧不足,是台灣人自古以來的做法。
如何印證番薯的歲月刻痕影響我們有多深,去查內政部的「地名資訊服務網」,會得到26個跟番薯有關的地名,番薯寮、番薯簽/籤、番薯厝、庄、里……到處都是,從北到南,涵蓋十幾個縣市。

其中,桃園客庄中壢的番薯里,客語的番薯(fanˋ shu,海陸腔)說起來就像華語的「飯蔬」,想想還真貼切,能夠作為主要糧食取代米飯的,確實只有蔬菜中的番薯,甚至是飼育豬隻的飼料,豬肉是台灣人最重要的蛋白質來源,更是一種象徵富饒的食物。
中壢豬埔仔聞名,因為黑豬知名品種桃園豬最大的交易市集就在中壢中榮里,有豬埔市之名,附近民生路靠近中平路一帶發展出養豬的周邊貿易,最重要的豬飼料蕃薯的各種加工品在此都能買到,有蕃薯市之稱,現在仍是重要的蔬果交易市場。
南方高雄旗山原名就是番薯寮街,自來就是貿易繁盛之地,傳說此處市街自舊街路南端土地公廟前開始發展,廟前茅草寮有阿婆賣番薯糜維生,是內門到里港之間往來商旅停歇裹腹之處,因而得名番薯寮。
台灣最具歷史風景的府城台南,最古老的中西區有番薯崎起自荷治時期,是賣番薯籤的小山丘,明鄭時期南明遺族朱術桂流連於此遙望消失的故國,荷據時期發展的第一條大道約略由大井頭到北極殿範圍。
雲林水林的番薯寮媽祖來台356年,座駕順天宮香火鼎盛,當年隨意搭個草寮安奉,年久寮上攀滿番薯藤,乾脆叫她番薯寮媽;現今已成為地方發展的核心,也是鄉土人文風景鼎盛之地。
台北大都會裡的萬華菜園里叫做番薯市,昔時艋舺番薯市皆是葛瑪蘭族人沿淡水河而上,在此與漢人交換貨物之地,最大宗的物資就是番薯,推估此地也是台北最早開發的所在,範圍大約是貴陽街二段、西園路、環河南路一帶;直到戰後初期仍然有熱絡的交易市集。
退休後才習畫的畫家謝招治,有一幅繪於2012年的作品名為《戰時生活的黑市交易》,又名《偷偷的賣番薯》的直幅水墨畫,自撰圖說為:「戰時市面上沒有生意可做,沒有收入來源,老百姓只好想辦法做一些黑市生意來維持生活,當時食物短缺的很嚴重,本來做水果買賣的叔叔和朋友合夥到農村去偷偷的批一些番薯來賣,鄰居得到了消息都趕來購買,一下子就賣光光了。」畫家的〈戰時生活〉系列是她84、5歲時回憶之作,困頓年代的番薯之美,仍然烙印於晚年的腦海中。
人類銘記於心的最終還是日日可見的飲食風景,番薯莫說傳統飲食,曾經一度能與麥當勞炸薯條媲美的就是頂呱呱的地瓜炸薯條和摩斯漢堡的黃金地瓜炸薯條,番薯和馬鈴薯抗衡,毫不遜色;台式點心蜜地瓜、地瓜圓在廟口或市場仍是熱門攤位,當然最讓人難以抗拒的是街角的烤蕃薯攤車,秋風起時,手裡握著熱熱的烤番薯,暖流升起,增添勇氣;這是多少二戰結束時,等待回鄉的台灣少年兵的日本鐵道月台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