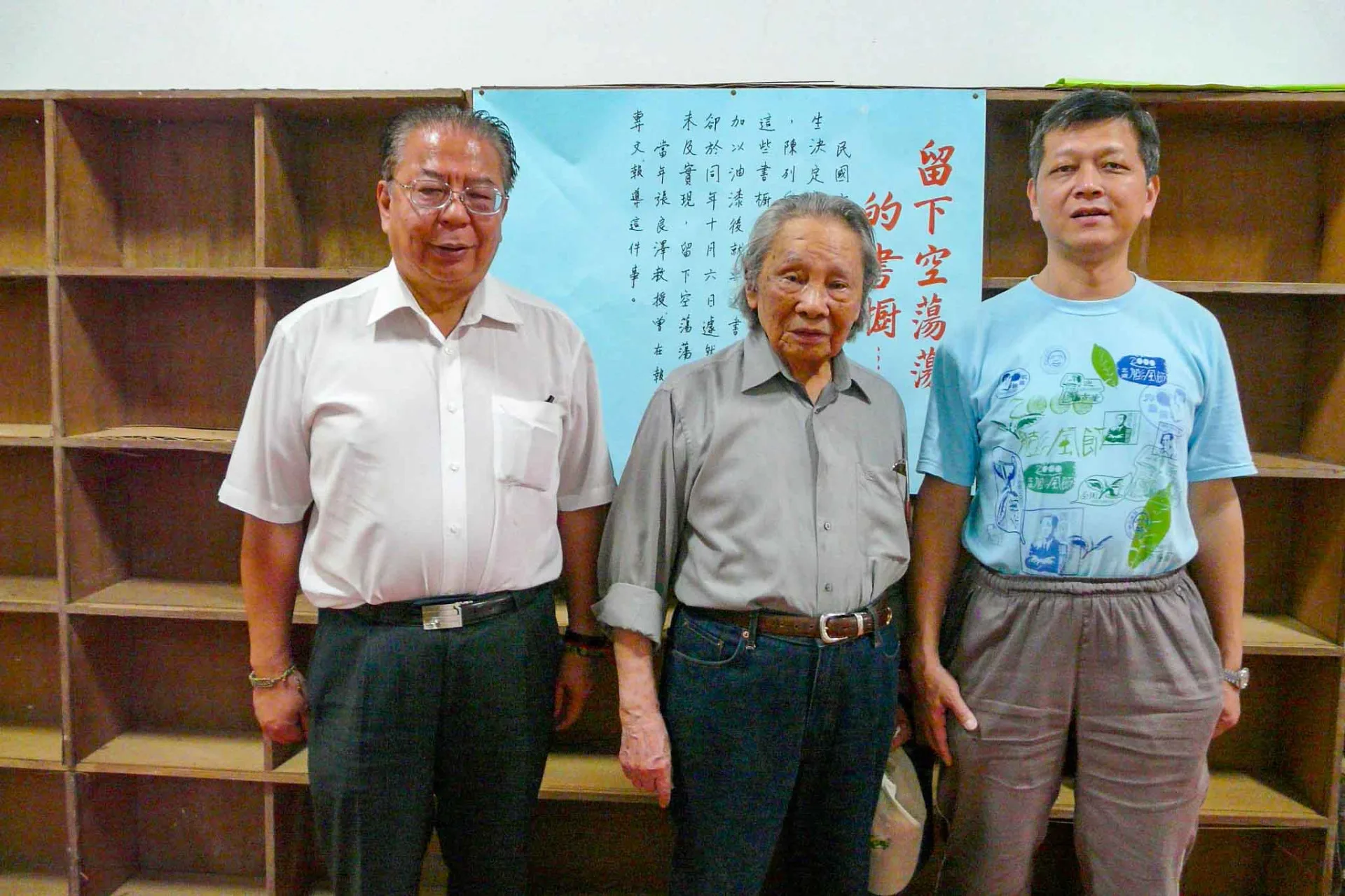文/楊國鑫
台灣客家研究的學者,長期研究客家歌謠及客家問題,現任教於新竹縣內思高工。
為什麼一位被譽為「台灣文學泰斗」的吳濁流,會在作品中唱起山歌?而他筆下的山歌,又究竟承載了什麼樣的文化與情感意涵?
在吳濁流的文學創作中,山歌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深具象徵與敘事功能的存在。綜觀其作品,山歌至少呈現出三層意義:第一,山歌象徵著快樂與自由;第二,山歌是庶民的聲音,而非讀書人的言語;第三,山歌是情感交流、甚至婚姻媒合的工具。
山歌,是快樂的聲音
早在1936年,吳濁流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水月〉中,就出現了山歌的描寫。作品描繪一位勞苦的農婦(男主角仁吉的妻子),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夜裡忙到十一、二點才能稍事休息。日間還得帶著嬰兒下田工作,牽掛家中其他孩子,又被監工嚴厲約束,幾乎沒有喘息空間。
然而,在她難得的一段哺乳休息時間裡,耳邊卻傳來其他女工與監工對唱山歌的聲音,那是一種興高采烈、充滿情趣的互動。
這段對比,凸顯了山歌所代表的輕鬆、愉悅、自由、甚至帶有調情意味的情境,它是庶民生活中短暫卻真實的快樂出口。對照女主角壓抑緊繃的現實,這樣的山歌顯得尤為鮮明,也揭示了「只有無憂的人才唱得出山歌」這層社會意涵。正如俗諺所說:「窮人毋使多,有兩斗米就會唱山歌。」

讀書人,不唱山歌
吳濁流最具代表性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共出現四次山歌描寫,其巧妙運用更令人拍案叫絕。第一篇〈苦練花開的時節〉中,他以「山歌如蛇蝎」埋下伏筆,直至最後一篇〈瘋狂〉,主角胡太明回家後突然跳上神桌,唱起山歌,隨即陷入癲狂狀態,戲劇性十足。
這不僅打破常規,更凸顯文學的張力與象徵性。神桌是家中最神聖的位置,而山歌卻是一種庶民娛樂,在「不該唱山歌」的地方唱山歌,這種衝突本身就展現了主角心靈的失序。山歌在此不再只是音聲,而是一種內心崩潰的外化表現。
與鍾理和、鍾肇政、李喬等作家作品中讓角色唱山歌相比,吳濁流可說是最早讓小說主角唱出山歌的作家。不過,《亞細亞的孤兒》中的山歌不同於傳統的七言四句男女對唱,而是一種節奏怪異、語調奇特的形式,呈現的是角色心理的扭曲與社會秩序的錯亂,與「文人不近山歌」的傳統價值形成強烈對照。
山歌,能娶老婆?
1956年,吳濁流發表短篇小說〈狡猿〉,這是他唯一一次在作品中使用正統七言四句、男女對唱的傳統山歌。劇情設定在新竹新埔一帶的橘子園——一個與一般常見的茶山不同的場景。原來新埔正是著名的椪柑產地,因此這樣的空間選擇,既寫實也巧妙。
小說中的主角江大頭與年輕的女工美珠初次對唱山歌,便深受她的歌聲吸引,最終甚至透過媒人與金錢運作,將美珠娶作小老婆。山歌在這裡,不僅是情感的觸媒,更是促成婚姻關係的實際工具。
吳濁流深刻掌握了山歌的文化功能,並將其納入小說情節之中,使作品不僅真實可感,也兼具文化厚度。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主角江大頭在小說中開口唱歌,但他並非作者本人的象徵,反而更像是庶民階層生活真實的縮影。
從〈水月〉到《亞細亞的孤兒》,再到〈狡猿〉,吳濁流筆下的山歌多面而深刻。它既是農民勞動中的慰藉,也是庶民生活中的浪漫;既是情感的寄託,也是精神崩解的象徵。吳濁流以山歌說故事、寫人生、抒心聲,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山歌在台灣文學中,不僅是一種聲音,更是一種文化的深層語言與歷史記憶的迴響。吳濁流小說中山歌的表現,令人驚嘆不已;他無疑是我心目中真正的世界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