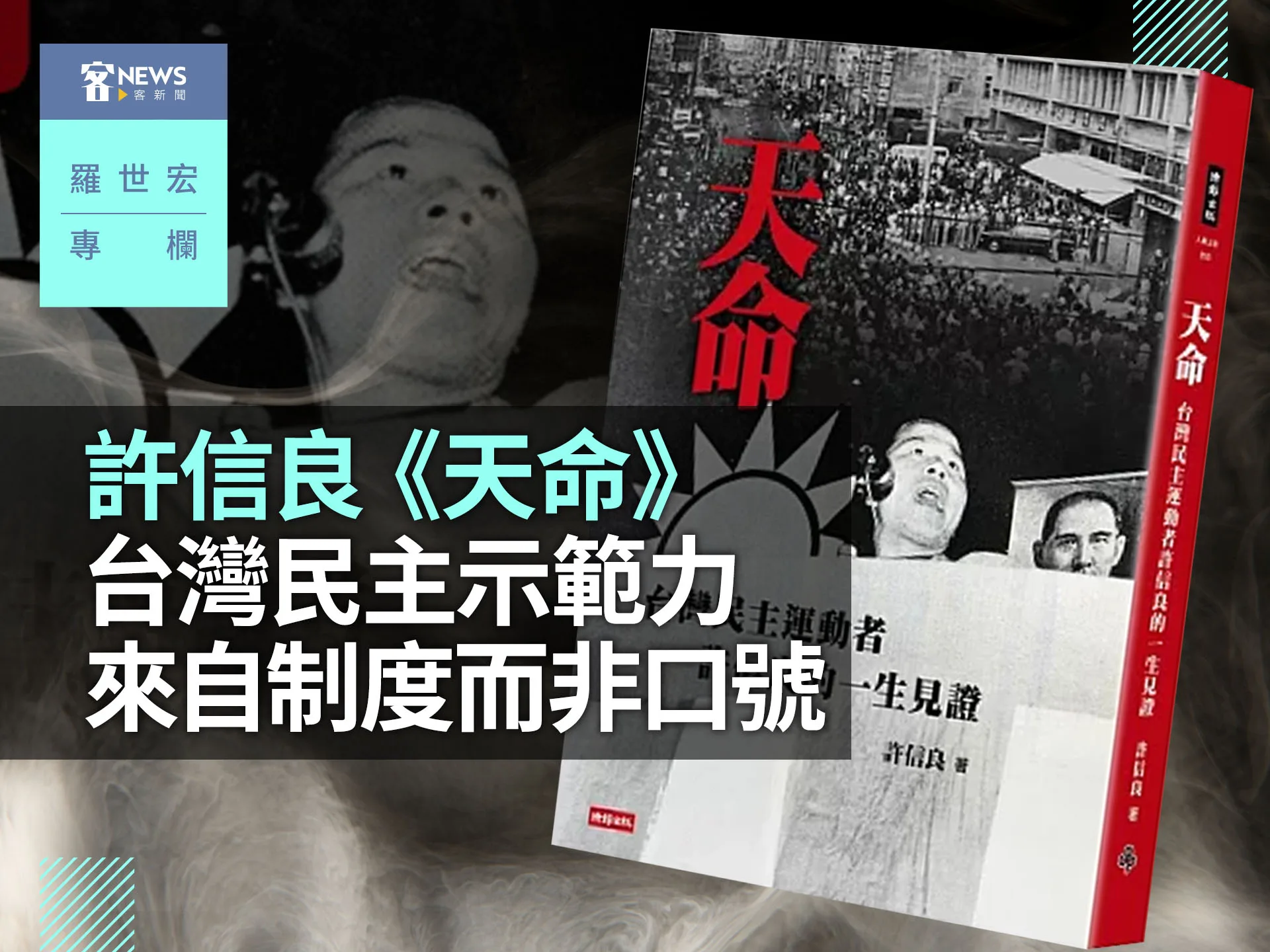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許信良在《天命》自序中,並未將視野停留在台灣,而是帶著相當大膽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的政治處境。他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能不能民主」,而是「什麼時候會走向民主」。這不是基於浪漫情懷,而是他基於對歷史循環的長期觀察。
1995年提出「大膽西進」時,許信良並不是呼籲投降主義,而是洞察到中國經濟開放所可能引發的社會變遷。他相信,在自由競爭中,台灣人會展現驚人的生命力;同樣地,中國人民也會因工業化與城市化而產生新的社會意識。這三十年的歷史發展確實印證了他的預測。台灣成為全球尖端科技中心之一,而中國則躍升為世界排名數一數二的經濟體。
在他眼中,這條歷史軸線使中台雙方都正在形成新的「新興民族」。不過,中國的這股力量被兩種力量牽制。其一是根深柢固的民族主義,使政治能量轉為排外與對抗;其二是不民主治理,使人民在制度上無法獲得充分的政治參與。
許信良觀察,美中對抗的本質不是兩國競爭,而是民族主義對全球化的反攻。他提醒,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都是民族主義對撞,而今日的關稅戰、科技戰其實正重演同樣的歷史模式。全球化不會死亡,但民族主義若失控,卻能讓一個國家自我毀滅。
對於身處美中之間的台灣而言,若不警惕民族情緒的蔓延,很容易落入「選邊站」的被動結構,而忽略民主本身的內在價值。而台灣社會若在內部仍維持族群界線與歷史對立,那麼在外部面對民族主義大潮時,也會失去自主判斷能力。
在談美國時,許信良特別指出,美國並非全球化的受害者,而是貧富不均的受害者。他引用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批判,指向美國高所得者與一般民眾之間的巨大落差。他在提醒台灣:如果民主不能處理社會不平等,那麼民主的吸引力就會下降。
無論是新住民權益、原住民族自治、青年貧窮、地方城鄉差距,若民主無法觸及這些深層議題,就難以證明制度的優越性,也更難對中國人民產生啟發。
在一段常被忽略的訪談中,許信良提到胡錦濤時期中國社科院來台考察民主時,他提出一套「成本最低、穩定性最高」的改革設計: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面改為直接民選。這意味著,中國不必採取劇烈的革命,也不需全面西方式制度移植,而可以從提升代議正當性開始,一步步走向民主政治。這是非常東亞式、漸進式、符合文化背景的改革路線,也比激烈對抗更有可能被中國社會接受。
許信良一再強調,台灣的民主示範力來自制度品質,而非政治口號。若台灣自己仍陷於族群動員、歷史傷痕、情緒選舉,那麼中國人民自然不會被台灣模式說服。反之,若台灣展現高品質治理、成熟政黨制度與社會凝聚能力,那麼民主就會成為華語世界的文明象徵。
這是他晚年思想最動人的地方。他並未把兩岸放入對立框架,而是放在文明競爭的座標上。他相信,在21世紀,人類的進步不再由帝國或民族力量決定,而是由哪一方能展現更成熟、更自由、更能整合差異的文明形態。
許信良手寫24萬字,其實象徵著一種堅持:台灣的民主來之不易,而下一階段的民主任務,更需要清醒、耐力與文明的高度。《天命》不是回憶錄,而是一部傳遞火炬的書。
許信良的「天命」之所以動人,不在於他所經歷的民主運動榮光,而在於他對未來仍抱持希望。對台灣,他期盼的是更好的民主;對中國,他期盼的是終將到來的民主化;對世界,他期盼的是超越民族主義的全球合作。這些願景都不是空談,而是基於他親眼見證的歷史經驗,也是他晚年最堅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