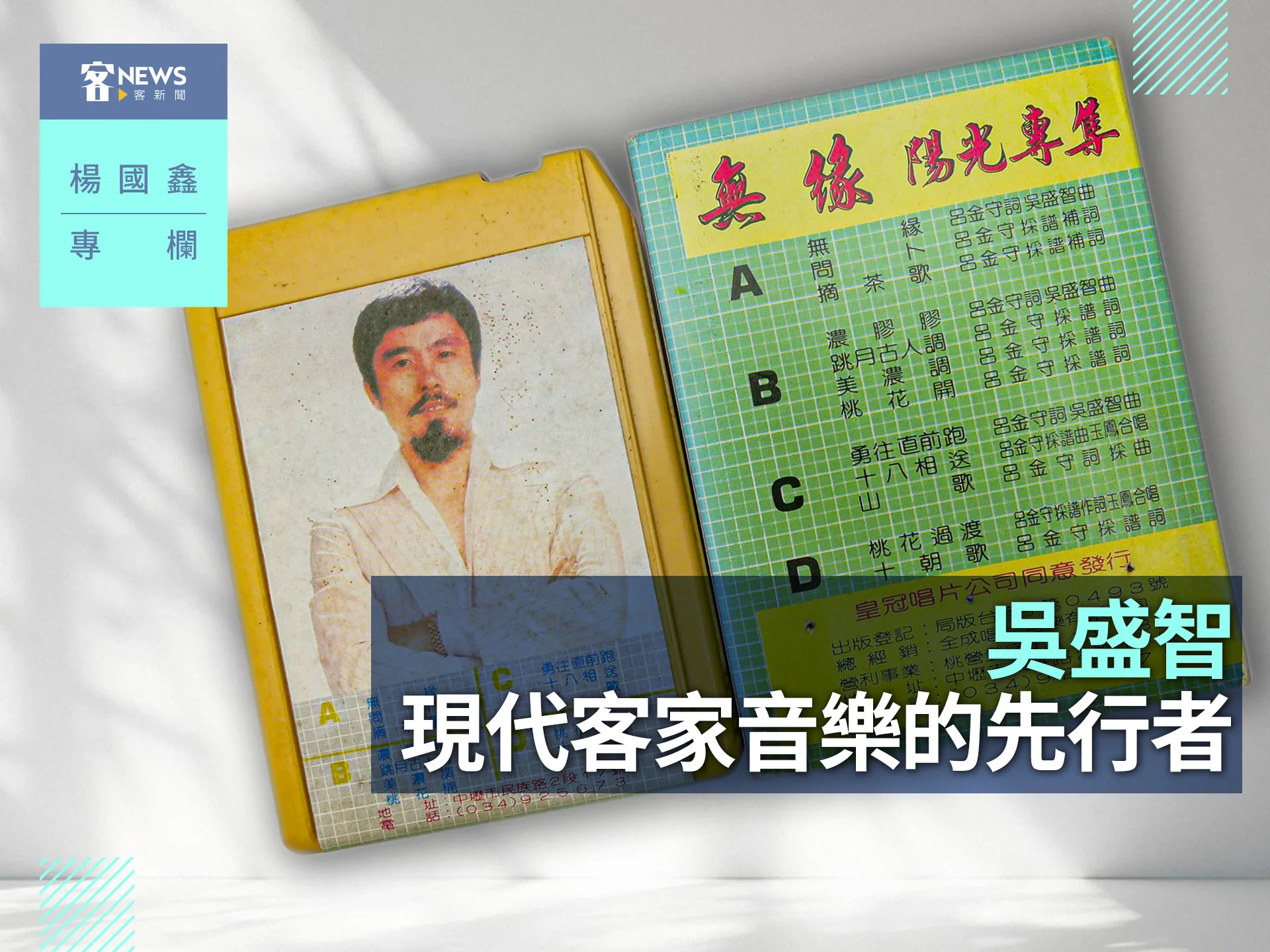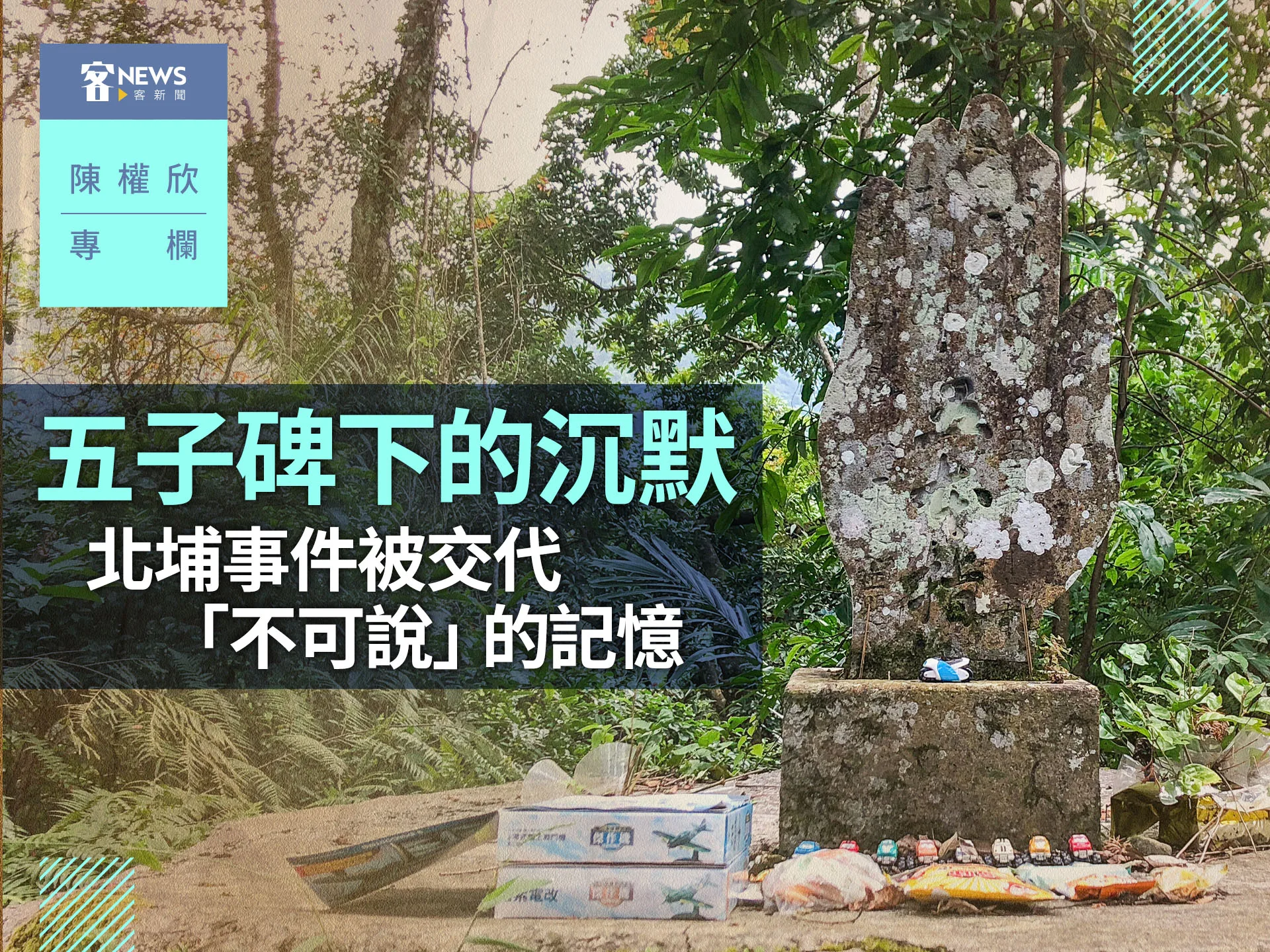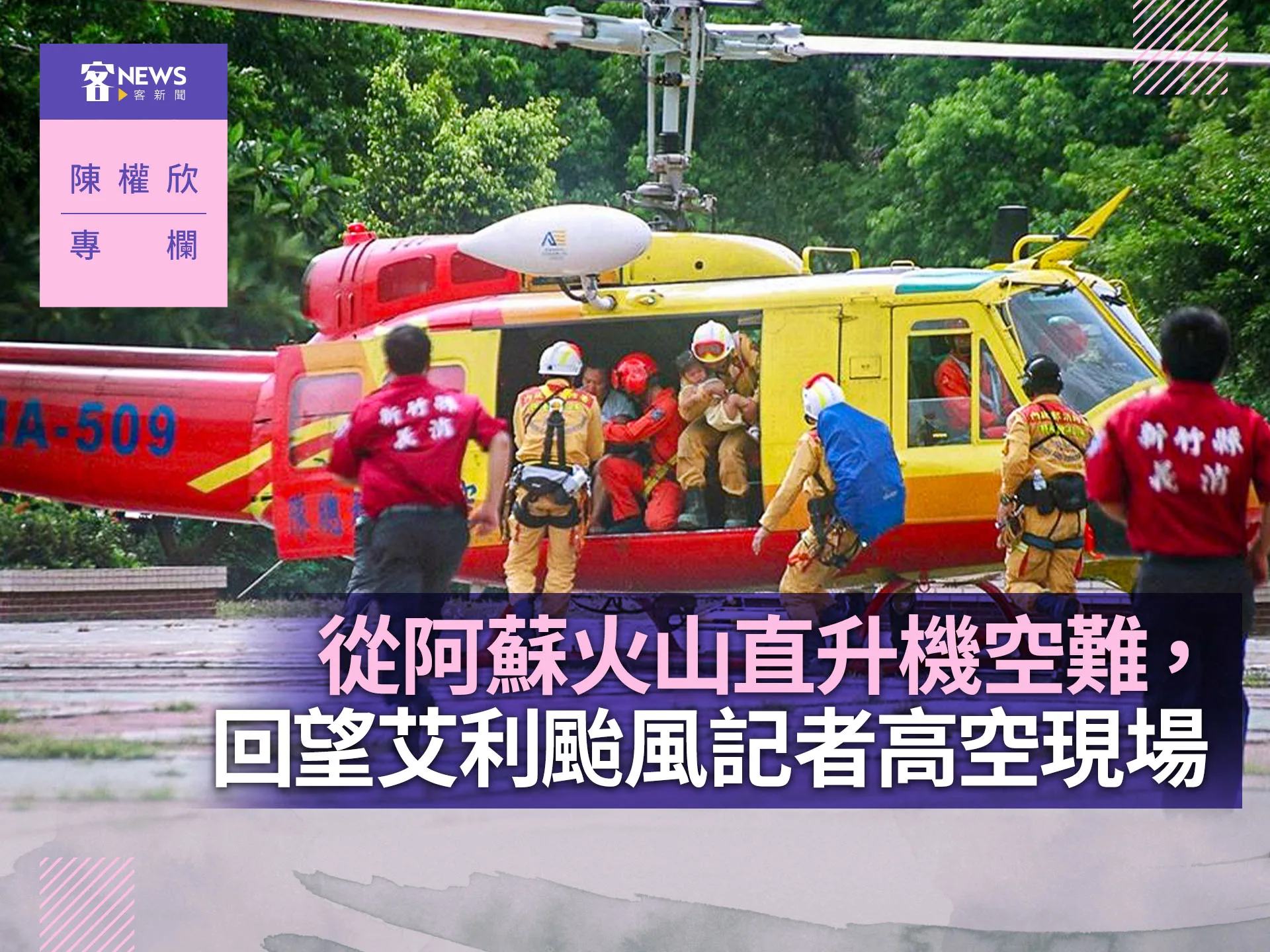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加勒比客家移民動因
客家人移民至加勒比地區,與當時殖民經濟轉向契約勞工制度息息相關。自1853年起,加勒比地區開始引進華人契約勞工。19世紀中葉,大量客家人被引進至當地的甘蔗種植園及其他殖民產業。契約期滿後,客家人在牙買加與蘇利南等地逐漸轉入零售業與小型貿易,並陸續展開第二波移民潮。
經濟因素之外,客家人移民加勒比地區亦與太平天國運動及土客械鬥等動盪事件密切相關。隨著太平軍勢力的起落,許多客家人被迫逃離家鄉。其中,逃至廣州—香港地區的客家難民,常向能以客家語溝通的巴色會傳教士尋求庇護。以洪秀全的部將洪桂陽(Hong Kuiyang)為例,他曾在香港接受巴色會庇護,改信基督新教,並於教會學校擔任教師。1872年,在黎力基(Lechler)夫婦的協助下,洪桂陽偕同其妻及多位香港巴色會信徒移民至英屬圭亞那(British Guiana),並於喬治城(Georgetown)建立教會。
土客械鬥亦引發大規模的流亡潮,數以萬計的客家人被迫逃亡。其中,許多人成為契約勞工,被送往秘魯的鳥糞礦工作地區與古巴(Cuba)。據記載,約三千名客家難民被帶往香港,其中一部分最終選擇離開中國,前往夏威夷、東南亞及西印度群島等地。
加勒比客家的分佈
加勒比海地區共包含13個國家,其中古巴(Cuba)、牙買加(Jamaica)與千里達及托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三國的客家移民歷史最為清晰可考。另,就加勒比共同體(CARICOM)而言,該區域組織目前擁有15個會員國。本集聚焦於其中與客家移民相關的國家,包括:蓋亞那(Guyana)(原英屬圭亞那,British Guiana)、法屬圭亞那(French Guiana)(法國的海外省,至今仍由法國直接管轄)、牙買加(Jamaica)與蘇利南(Suriname)(原荷屬圭亞那,Dutch Guiana)。
加勒比共同體成立於1973年其主要目標為促進成員國間的經濟合作、貿易發展、外交政策協調、社會進步與區域整合。因此,在討論「加勒比地區的客家人」時,所指涉的範圍不僅限於地理上的加勒比海諸島,亦包括加勒比共同體內與客家移民有歷史聯繫的若干成員國。簡言之,客家人在加勒比地區的分布主要涵蓋古巴、牙買加、千里達及托巴哥、蓋亞那與蘇利南等國。
契約勞工制度的復興
十九世紀加勒比地區勞動結構的轉變,主要受到奴隸制度廢除的驅動。奴隸制度的廢除從根本上改變了當地的勞動體系。首先,獲得自由的奴隸多轉向追求獨立的小農經濟,選擇離開種植園,尋求自主經營的生活方式;其次,自由勞動者挑戰了傳統的種植園勞動管理模式,根據自身需求決定是否參與勞動市場,導致種植園主難以有效掌控勞動力;再者,勞動力短缺與工資上升進一步削弱種植園經濟的穩定性,部分原因在於原奴隸轉向薪資較高的其他工作,或選擇減少工時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在這些變化壓力下,種植園主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薪資以吸引並留住勞動力,加重了其經濟負擔。
為了應對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契約勞工制度的恢復成為關鍵策略。1838年,英屬圭亞那率先試行契約勞工制度,隨後於1845年至1848年間,該制度在千里達、牙買加等地被制度化並加以推行。契約勞工制度為種植園經濟提供了勞動力的穩定來源,成為支撐經濟運作的重要基礎。
19世紀的契約勞工制度以亞洲人為主要勞動來源,特別是來自印度與中國的移民。種植園主通常透過支付船票費用、提供獎金等方式主動參與招募與移民安置,並與勞工簽訂明確的契約期限。在千里達與英屬圭亞那等地,契約勞工成為甘蔗種植園經濟的主力;相較之下,牙買加對契約勞工的依賴程度則顯著較低。
客家移民在加勒比地區的早期經濟活動
早期客家移民在加勒比地區主要參與勞動密集型的殖民經濟產業,尤其集中於甘蔗種植業。他們多在契約制度下進入種植園工作,承受嚴苛的勞動條件。在古巴,客家勞工在華人社群中扮演了甘蔗種植園勞動主力的角色;在牙買加,客家契約勞工同樣在甘蔗產業中從事艱苦勞動。
隨著契約期滿,許多客家勞工開始憑藉社群內部的互助體系及資源調配,逐漸轉向零售與小型貿易活動。在牙買加,客家人迅速從契約勞工身份轉型為零售業者,廣泛開設雜貨店(當地稱為 Chiney shops,可參考江明月導演的作品:唐舖),並在鄉村與城市經濟中發揮關鍵作用。在蘇利南,客家群體則發展出以零售與餐飲為核心的經濟模式,依靠語言與家族網絡,建立起強大的社群支持系統,鞏固其經濟地位。
在古巴,完成契約後的客家人多選擇於哈瓦那等城市經營小型商店,商業活動主要集中於食品零售與貿易領域。至於英屬蓋亞那,客家契約勞工則透過有限資本與社區信貸網絡,逐步進入零售與貿易市場,經營提供當地市場所缺乏商品的小型商鋪,顯示其高度的經濟適應力與社群協作能力。
互助會系統對客家契約勞工的影響
互助會系統(即「標會」)在客家契約勞工創業與社群建構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除了協助個體從事零售業與商業活動外,互助會亦強化社群內部的社會凝聚力。此制度為華人社群在加勒比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嵌入提供了制度性支持與資源動員的基礎。
在牙買加,互助會有助於華人社群在當地經濟活動中取得立足之地。輪標(rotating)信貸體系的運作,不僅促進了零售業的擴展,也支撐了客家社群對傳統文化的維護與對主流社會的融合。華人慈善協會等機構,透過財務支援與社會服務,進一步強化了社群的內部連結與向外連結的能力。
在英屬蓋亞那,客家契約勞工利用社區信貸機制擴展零售業務,實現經濟自立與向上流動。小型商店經營者透過互助會籌資,販售進口食品與服飾等當地市場缺乏的商品,進一步促進地方經濟的多樣化。同時,客家社區組織也重視教育與財務支援,為下一代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與文化延續的基礎。
在千里達及托巴哥,客家契約勞工及其後代則依靠家庭儲蓄與社區網絡,開設小型商店並透過互助合作推動商業發展。客家互助會的存在促進了社區內部資源共享與經濟互惠,也成為維繫社群文化與社會支持的重要機制。
古巴方面,客家移民透過互助會從事食品零售,進一步推動零售行業的多樣化發展。總之,標會制度為客家契約勞工在缺乏正式金融體系的殖民地社會中,提供了一種安全且靈活的資金管理與籌資途徑,使其能投入商業、購地與其他家庭經濟活動,進而穩定經濟基礎、提升社會地位。此制度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組織機制,促進了客家社群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的嵌入與文化保存。
客家語言在加勒比地區的克里奧化
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客家語曾是加勒比地區多個國家華人社群的主要語言,特別是在契約勞工移民群體之中。以蘇利南為例,源自中國廣東惠東安地區的移民將當地方言「惠東安客家話」帶入當地,並在19世紀中期成為華人社群中的主要語言。在牙買加,客家話亦是早期華人社群在家庭與社區內日常溝通的主要語言;而在千里達,客家話作為早期移民的核心語言,對社群身份的維繫與文化價值的具有關鍵意義。
然而,隨著社會語言環境變遷,客家語的使用逐漸衰退,尤以第二代與第三代移民為甚。在蘇利南,荷蘭語與蘇利南的斯拉納通戈語(Sranantongo)、當地的克里奧語(creole language)的普及,加上講華語移民的持續遷入,使得客家語在年輕世代中快速式微。在牙買加,官方語言英語與廣泛使用的Patois(當地的克里奧語)對客家話的傳承造成壓力,使得年輕一代漸漸放棄使用客家語。在千里達,年輕一代日漸融入主流社會,以英語作為主要日常語言,對客家語的需求與認同感相對減弱。
儘管如此,在部分年長華人群體中,客家語仍於家庭聚會與社區活動中保有一定使用頻率。在蘇利南,有部分客家後裔積極透過語言課程與文化活動推動語言復興,藉此保護族群文化遺產。在牙買加,長者仍在家庭聚會場合中使用客家語溝通。在千里達,老一輩移民也持續在家庭與社區場域中使用客家語,作為表達族群文化身份的重要方式。
客家語不僅是日常溝通的工具,更是族群認同的象徵。在加勒比地區的移民經驗中,客家語作為文化傳承的媒介,成為連接過去與當下的重要橋樑。然而,語言的流失對族群身份構成挑戰。新一代客家人多以當地主流語言接受教育,使得母語使用率降低,進而削弱了語言在身份建構中的功能。
此外,隨著語言接觸與遷徙歷程的演進,客家語在不同地區的使用模式亦呈現多樣化。在某些地區,如蘇利南,客家語已與當地語言(如斯拉納通戈語)發生語言交融,呈現出語言接觸與創新發展的現象。
客家語在加勒比地區的命運受到代際傳承、文化融合與主流語言壓力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雖然使用範圍持續縮小,客家語仍以文化象徵的形式存在於特定社群中,並看見他們透過各種努力持續推動保存與傳承
客家的克里奧化(Creolization)現象
加勒比地區的客家移民潮始於19世紀中葉,主要來自中國南方,尤以深圳與東莞地區為主。初期,這些移民多從事甘蔗種植等勞動密集型的殖民經濟工作。然而,隨著契約期滿與在地適應的深化,客家人逐步進入商業領域,並於當地社會中形成具有獨特性質的文化身份。在這個「在地化」的進程中,客家人在語言、文化與族群邊界之間展開持續協商,特別是在牙買加與蘇利南等地,逐漸建構出一種「華人—加勒比」的混合身份。客家文化在與非洲裔、歐洲裔及原住民文化互動的過程中,展現出高度的融合能力。通婚現象亦推動了文化混合的發展,尤其是與非裔女性的通婚,催生出「半華人」身份,此一族群位置反映了客家文化與克里奧文化的交會與再創造。儘管如此,客家人仍保留了若干文化傳統,同時吸收當地文化特質,形成具有在地特色的新型「客家性」,一種克里奧客家性。
語言適應之外,宗教實踐也是文化融合的重要場域。在加勒比地區,客家移民在保留祖先崇拜的基礎上,廣泛接納基督教元素,逐步發展出混合的宗教身份。在古巴,客家人的宗教實踐融合了傳統中國信仰、非洲宗教與天主教特質,產生了如 Sanfancón(融合中國武聖關公與非洲神祇特質)的混合型神祇。在牙買加,客家人調整基督教儀式,將其應用於婚禮與喪禮等生命禮俗中,並持續保有傳統祖先祭祀。千里達及托巴哥的客家社群,則在基督教節慶中融入中國傳統節日元素,如農曆新年與中秋節。在多元宗教共存的蘇利南,客家人的祖先崇拜歷經轉化與簡化,清明等祭祖儀式的實踐形式亦有所調整。
在認同建構的層面,客家人與加勒比地區非裔、印度裔等族群的持續互動,不僅促使其重新界定自身於當地社會中的族群位置,更促成一種具混融性的新文化主體的誕生。透過語言轉變、宗教融合、經濟參與與日常生活實踐,客家人在加勒比地區逐步形塑出一種既延續傳統、又深度在地化的文化身份——克里奧客家性。這種克里奧客家性並非單純的文化妥協或同化結果,而是一種在多元文化條件下,族群主體透過實踐與協商所產生的文化創造力的展現。它體現了族群身份的再建構,也反映了客家社群如何在跨族群互動中重組其文化資本與認同方式,將傳統客家元素與加勒比在地文化交融轉化,生成新的文化形態與認同語彙。
點我線上收聽《客座教授!安烈炫》
《講客廣播電臺》邀請國內3位重量級客家學者張維安、羅烈師與林本炫,共同主持客家知識含金量超高的廣播節目《客座教授!安烈炫》,將嚴肅的族群文化與客家議題,透過輕鬆對談的方式,傳遞給大家,把學術研究和民眾的距離,拉得更近一點。
您還可以透過以下平台隨選收聽:
Apple Podcast ▶️https://reurl.cc/yLy3bl
Spotify ▶️https://reurl.cc/Dj1VpN
SoundOn ▶️https://reurl.cc/Gj9o2D
KKBOX ▶️https://reurl.cc/Wx5kK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