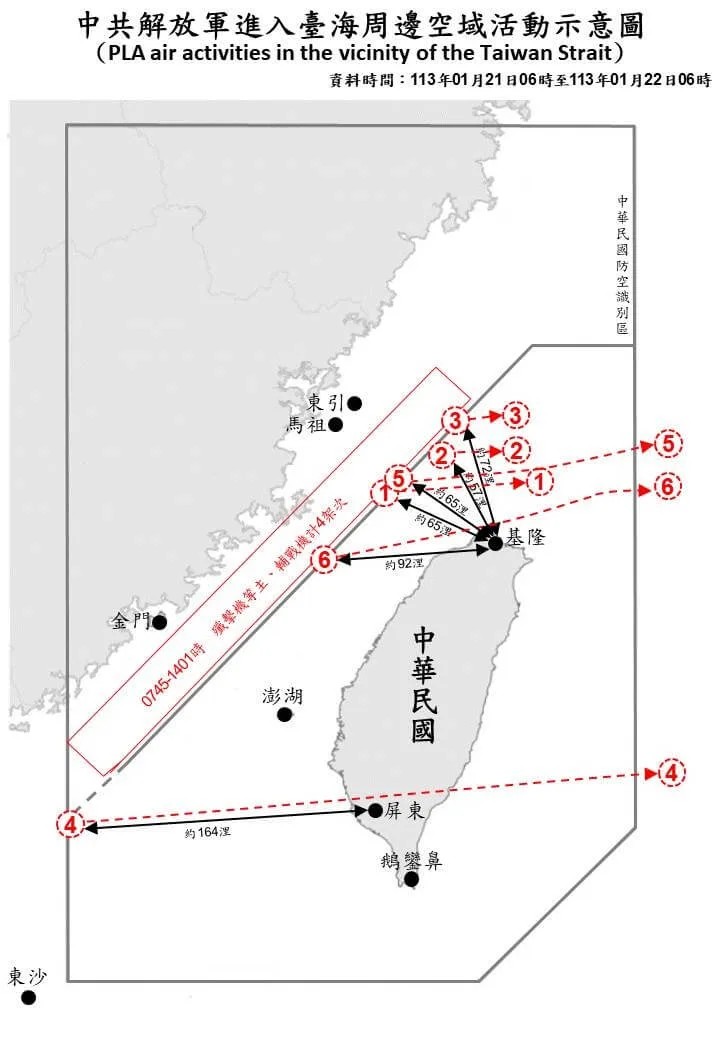文/蕭秀琴
曾任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作家暨譯者,著有《料裡風土:往山裡去的地方,九種食材從山到海建構客家飲食》、《料理臺灣:從現代性到在地化,澎湃百年的一桌好菜》等書籍。現居離台北城約一個小時的小鎮,持續文字工作。
客家人的鹹菜是百變女神,是觀音千手千眼的風物,從初階的水鹹菜、中階的卜菜/覆菜,到高階的鹹菜乾,天天煮365道絕對不是問題,不信,試試卜菜白醬奶油螺旋麵,濃稠奶醬裡的鹹顆粒,有口感的麵和切得細碎的卜菜相互提升不違和。
做一件事如果需要用到八九個步驟,能有十個以上的形容詞,並難以被轉譯,這種精確性與獨特性的用語是一個族群的資產,客家人的「鹹菜」一詞,或許可以這麼說——台灣客家人的文化遺產。
日文有一個形容秋光的詞是「木漏れ日」,形容陽光從樹葉縫隙中灑落的樣子,據說是全世界最難被轉譯的形容詞,浪漫台三線上客家人的「滷鹹菜」(luˋ ham coiˇ,海陸腔)也是,集形容詞、專有名詞、動詞於一,在島嶼十一月中開始持續到來年二月結束告一段落,然而仍是未完成式,因為在接下來的一整年,都能變著花樣完成它。
九降風吹日光閃爍,客家人說「風合日」(fungˊ gagˋ ngidˋ,四縣腔)的日子,是斬(zamˊ)大菜的好時機,滷鹹菜之前,芥菜要用陽光讓它柔軟,砍下來的菜——大菜確實厚重到需要用砍,砍客家人說斬,活靈活現如古裝劇裡的戰爭場面——一棵一棵排好如此壯烈親炙熱陽,每一面經歷兩三個小時的洗禮,再貶轉來( bienˊ zhonˊ loi,海陸腔 ,翻過來之意),翻面再曬,「曬鹹菜」半天過去,冬天日光短,正逢下課的小學生可以被使喚,幫著做,不停歇的工序直到燈火亮起,晚餐上桌。
禾埕堆得像小山般的大菜,每一棵都要挲鹽(soˋ rham,海陸腔),這個動作,講究的主婦決不準小孩動手,用雙手輕柔摹挲呵護,除了在客家婆媽幫嬰兒洗澡洗頭時常看到之外,就是此刻了,所以她們絕不假手他人。
用了鹽再開始揉(ngioˋ,海陸腔)鹹菜,這個動作,要保證不會把鹹菜折斷、弄破皮才能夠參加,納悶她們到底是要用力還是不用力才會把鹹菜揉到可以放缸裡不會被壓斷、踩斷,踏(tabˋ,海陸腔)鹹菜可是很多人的美好童年回憶,整個過程中唯一會被拜託幫忙的工序,因為一般家用容器,再大的缸也只能容小孩在裡面踩踏。
天色已暗晚餐前,工事告一段落,滿缸的鹹菜要讓它出水,壓個兩三顆大石頭幫他增進速度叫矺(zag,海陸腔)鹹菜,這詞很難找到華語字替用,用石頭壓緊還要撨對位置以免無功用,不會比撨代誌簡單。小時候讀司馬光打破大水缸的故事,老師說得興起我腦海也浮想聯翩,就想到矺鹹菜把菜缸打破,果真就被我打破了,還真叫心想事成。
日光燦燦風合日,台三線上難得乾燥的日子,十天半個月水鹹菜完成,日常三層肉鹹菜湯,假日家聚功夫一點,鹹菜、豬肚和紅蘿蔔紮得像柴薪煲一鍋豬肚湯,鹹菜鴨湯可以簡單也可以繁複,端看想喝湯還是想吃肉。
至於炒一大盆鹹菜肉絲好裝罐,讓住宿的中學生帶回宿舍,則是每週日的大工程。高中時代最飢餓的一道料理是同學們圍著一盒又油又酸甘甜的鹹菜炒肉絲,一人偷一口,讓興沖沖帶著來上學的人,又要再等五天才能解饞。
剛開缸的水鹹菜去掉一些葉子,三層肉切細一些煏油,蒜末剁碎,起鍋前勇敢的灑一把二砂糖讓它來不及融化,裝盒帶到學校交流比較。
煮什麼都摎(lauˋ,海陸腔)一點水鹹菜的期間,也算是冬日限定了,至於亼鹹菜(cibˋ ham coiˇ,海陸腔),那又是另一個濕醞(shibˋ yun,海陸腔)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