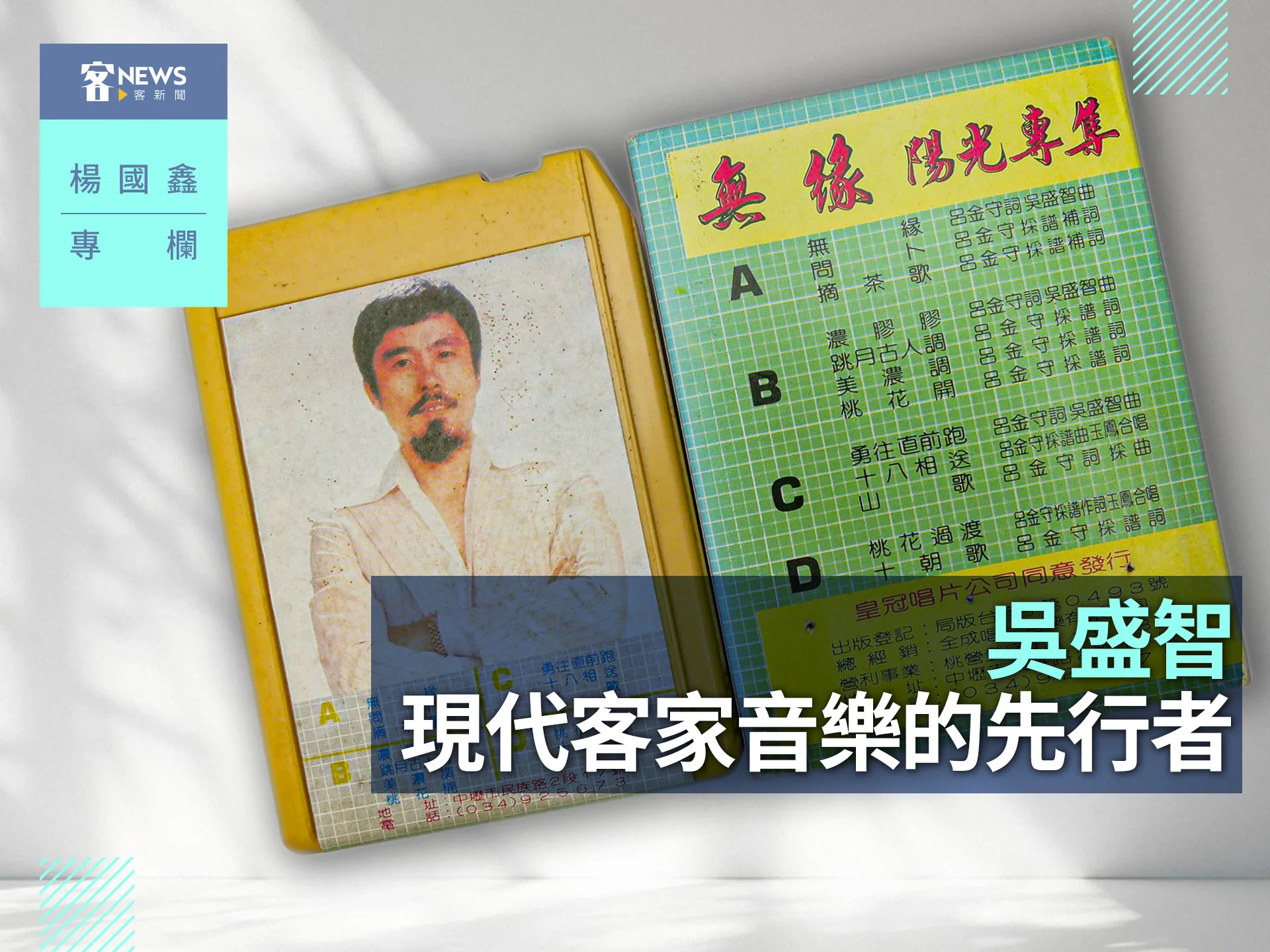文/蕭秀琴
曾任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作家暨譯者,著有《風物季語》、《料裡風土》與《料理臺灣》等書籍。現居離台北城約一個小時的小鎮,持續文字工作。
曾經被李旺台先生指正過,「我們不會說自己是六堆人,我是竹田人,曾貴海是佳冬人……」趕上讀台灣史的風潮,我被朱一貴事件與客家史植入新名詞並感到興奮,去過佳冬朝聖,或許搭南迴線時在自強號快速的駛過「有個小小的竹田火車站」(作者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播磨丸》的序章第一段第一行)時,在不經意的一瞥中記住了「竹田車站」,大部分的台灣人知道「六堆」這個名詞不會超過二十年,拜客委會行銷「地方」之賜,六堆成為認識南客的關鍵字。
《亻厓屋下个番檨樹》是作家出版過五本長篇小說之後,收錄十個短篇小說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並且是以他的母語客語創作的作品,而這個創作歷程正好讓我們理解李旺台的創作核心以及客語寫作的意義。
讀過他的長篇小說的讀者都曾被翻開書名頁之後,印象深刻的句子打動:
本書獻給
出生成長於日治時代,換中國國民黨治台後,終其一生重新學習、重新適應、努力順服以及努力不順服的所有台灣人。
這個創作核心連貫到本書的第一篇小說,也是作為書名的〈亻厓屋下个番檨樹〉,戰後一個客家家庭,在引揚歸日的校長善意引薦下,搬入日式宿舍生活,及後來被國民政府要求歸還搬離後的情感傷痕,一位騎腳踏車賣布的「大道商人」(だいどうしょうにん,街頭攤販)與妻子和他的三個女兒,以及被招弟來的兒子,在有芒果樹的院子裡生活是甜蜜的,主角是二女兒以第一人稱敘事,情感核心建立在充滿溫暖氣息的房子裡,不論是搬入與遷移,在芒果樹下或擠在閣樓裡,「澢澢汀汀个番檨汁係黃个,鮮嫩鮮嫩个黃,大口大口咬落去,再用力吞落該汁,香甜還有息把酸味,酸甜酸甜,係世間一等个味緒。」芒果的滋味象徵著家庭根源與生命情調。
接下來的九個短篇很快地進入了當代場景,有戰後嬰兒潮一代的退休養老人士的〈何老師最後个該兜日仔〉。〈雜貨店風暴中〉在離火車站不遠的地方開雜貨店的阿樹伯跟妻兒的拉扯拔河,他為了多賺一點錢二十四小時待命,三個兒子為了難以入眠的母親貼出「非營業時間恕不開門」。
在縣府擔任公務員的女性科長的〈想望〉,從被要求〈招娣妹〉的女孩到帶著老師跑到東南亞招生的校長,去中國做生意開爆竹工廠的生意人終於〈爆了發了〉,被政策鼓勵的檢舉達人得到獎勵的〈義士〉,傳統伙房灶下的老鼠稱作錢鼠,因為善待錢鼠發財卻把兒子養成「畜老鼠咬布袋」的〈金龍屋下个錢鼠〉,以及白天當老師晚上變學生「擔竿無齧愛顧兩頭,實在無結煞,難耐豺。」蠟燭兩頭燒的〈監考〉老師。

其中〈美創仙子〉以2015年八仙樂園塵爆案的受害者為描摹對象,小說裡從事新娘化妝的洪麗雲在八仙塵爆中失去了引以為傲的容顏與聲音,父親是一位有著「缺嘴」(兔唇)的西裝師傅,母親一直幫趁著天生靚妹的她成為網紅,是必排隊才能預約得到的美妝師,以美為生之人毀容失聲比死還嚴重,而她能夠轉念、配合醫療復健活著,依賴的是同樣有顏面傷殘的阿爸。
這個短篇是典型的李旺台風格,具有時代意義,人物描寫靈動有趣,個性面貌具體又兼具普遍性——台灣人獨特的精神風格與價值觀,是一篇很適合當做教材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以客語創作,展現了地方特質,因為語言代表了內在底蘊。
當然這些故事映照出李旺台個人的執念,每一個短篇都有反覆出現的時代面貌,或許跟他的記者身份有關也或許是他將此作為使命,在此時此刻的台灣社會——小說裡的每一個人物展現的不在於人應作出何種道德選擇,而是在追問所謂的「選擇」是否真正存在。
〈亻厓屋下个番檨樹〉溫暖厚道的一家人選擇吞下去;〈雜貨店風暴中〉同仇敵愾的三兄弟選擇擴大事端,否則無以改變現狀;〈何老師最後个該兜日仔〉是耄耋之年為氣喘所苦的何老師在最後的日子要不要做PCR急救,委託一個外人李先生來做決定,凡此種種都是目前台灣社會每一個人都可能面臨的問題。
若說普遍被認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短篇小說集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都柏林人》(Dubliners)以近乎冷峻而節制的筆法,描繪都柏林的情感與精神癱瘓(paralysis),李旺台的這十個短篇就是以溫柔而節制的筆法把「六堆人」的「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正式的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雖然溫柔一向不為文學語言所稱頌,幸而他以客語寫作讓作品有了靈動而深邃的意義。
《都柏林人》常被視為現代短篇小說形式成熟的重要里程碑,一部會隨讀者年歲增長而不斷改變面貌的書,這是因為喬伊斯不以戲劇化情節引人注目,而是在平凡中揭露人性的裂縫;《亻厓屋下个番檨樹》的十個故事沒有一篇高潮迭起,甚至讀者都能預料結局而仍然被吸引,在於每一個人物的都可能是每一個人的情感投射,以及用嶄新的句法讓你追隨下去。

客語中的語助詞,疊字狀聲詞,將名詞作動詞表達事物的情緒與細節,猶如〈美創仙子〉所以是吸引人的成熟小說,沒有落入記者報導文學的筆法,在於即便是憤怒、悲傷,或強烈的情緒描述都那麼的新穎,「『……妳盼得看𠊎像鬼樣仔生存下去吓?』講煞開始聲失失吔噭到抽胲另命,博噎毋轉。」講完痛哭之前,在客家人來說,最高的境界是「聲失失」失去聲音的瞬間,而才會「噭到抽胲另命」脖子抽到像不要命一樣甚至不停打嗝,而這是真的會發生的物理性樣態。
《都柏林人》至高境界的一篇〈死者〉(〈The Dead〉)被譽為無法超越的短篇小說,評論家 Sheila O’Malley認為「喬伊斯在此展露出極為坦誠的情感深度。」故事裡的情感深度有時候是透過描景寫物抵達,〈死者〉結束在「當他聽見雪微微飄落,穿越整個宇宙,輕輕降下,宛如最後終局的來臨,覆在所有生者與死者之上,他的靈魂也隨之緩緩沉醉。」而有時候是人物的心境轉折與刻畫,在另一篇〈伊芙琳〉(Eveline)中,「她把蒼白的臉朝向他,神情被動,如同一隻無助的動物。」
喬伊斯用愛爾蘭化英語(Irish English / Hiberno-English / Anglo-Irish)刻畫「都柏林人」最為人所讚頌,相較而言,直接以客語寫作打破台灣華文創作善用的抒情語調,就能同時突破平凡的框架與做作的口氣,最重要的是剛好消滅成語使用機會。
像是描述燒燙傷患者的面貌往往殘酷而不忍下手,此時面目全非的成語或許也完成了段落,而李旺台運用南四縣客語描繪,甚至會讓人聯想到六堆名物花生豆腐的製法,而且是嶄新的面貌;〈美創仙子〉包著紗布的右眼如是「目汁對麗雲該隻左眼流出,一滴又一滴,續下來目汁濫泔。包等个右眼下背也溚濕,紗布項个目汁由一條濕痕漸漸吔濕到歸塊仔,像正做好溫燒溫燒个豆腐面項攤个紗布。」
用客語南四縣腔創作可以將人物放回「六堆」,同時能夠顛覆(destabilize)標準華語的穩定敘事的表層,讓標準不再理所當然,而以語言為地方定位、去中心化,讓人物的社會階層、身份背景、地理區域與教育程度,直接透過語氣與句法浮現,接近上乘之作。
以標題中的「呢呢哪哪」(niˇ niˇ noˇ noˇ,四縣腔)作結,這是《亻厓屋下个番檨樹》主角拒絕同班同學、也是繼一家被要求搬離後,進駐日式宿舍的外省家庭的女兒採芒果的邀約後在內心喃喃自語,「𠊎心肚仔呢呢哪哪。」把想法放在心裡,也是一種敦厚的節制,一如這本書的大部分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