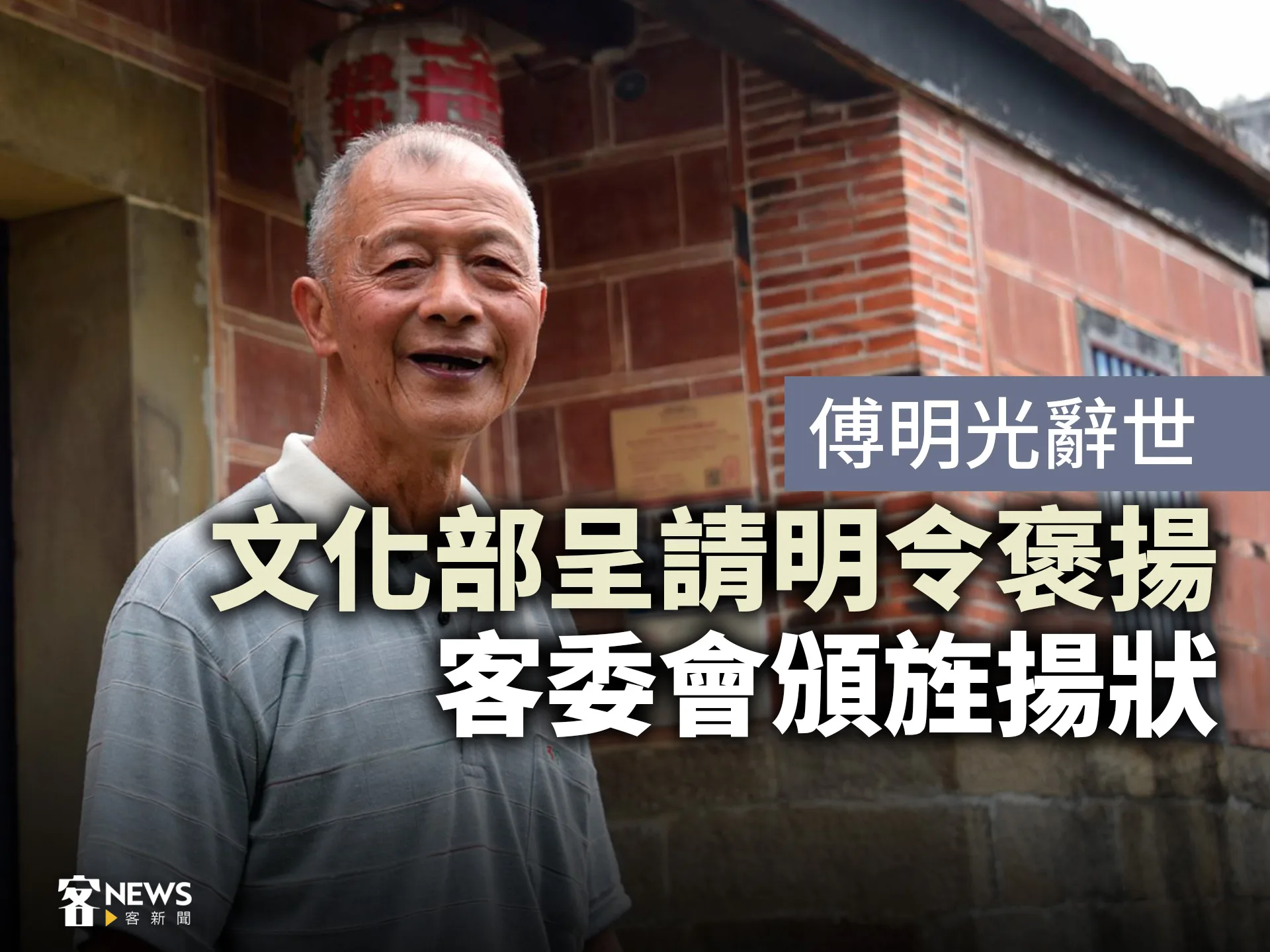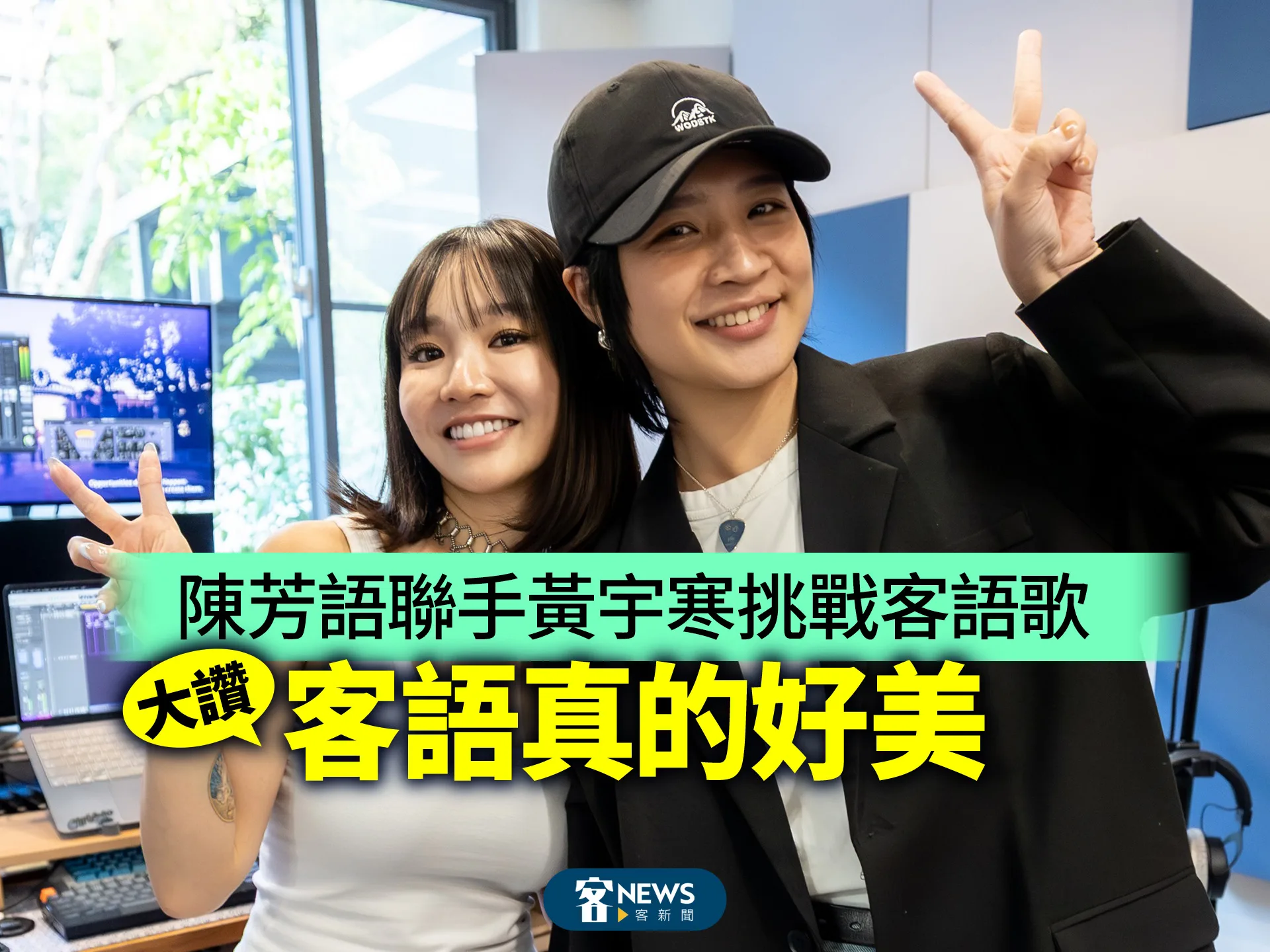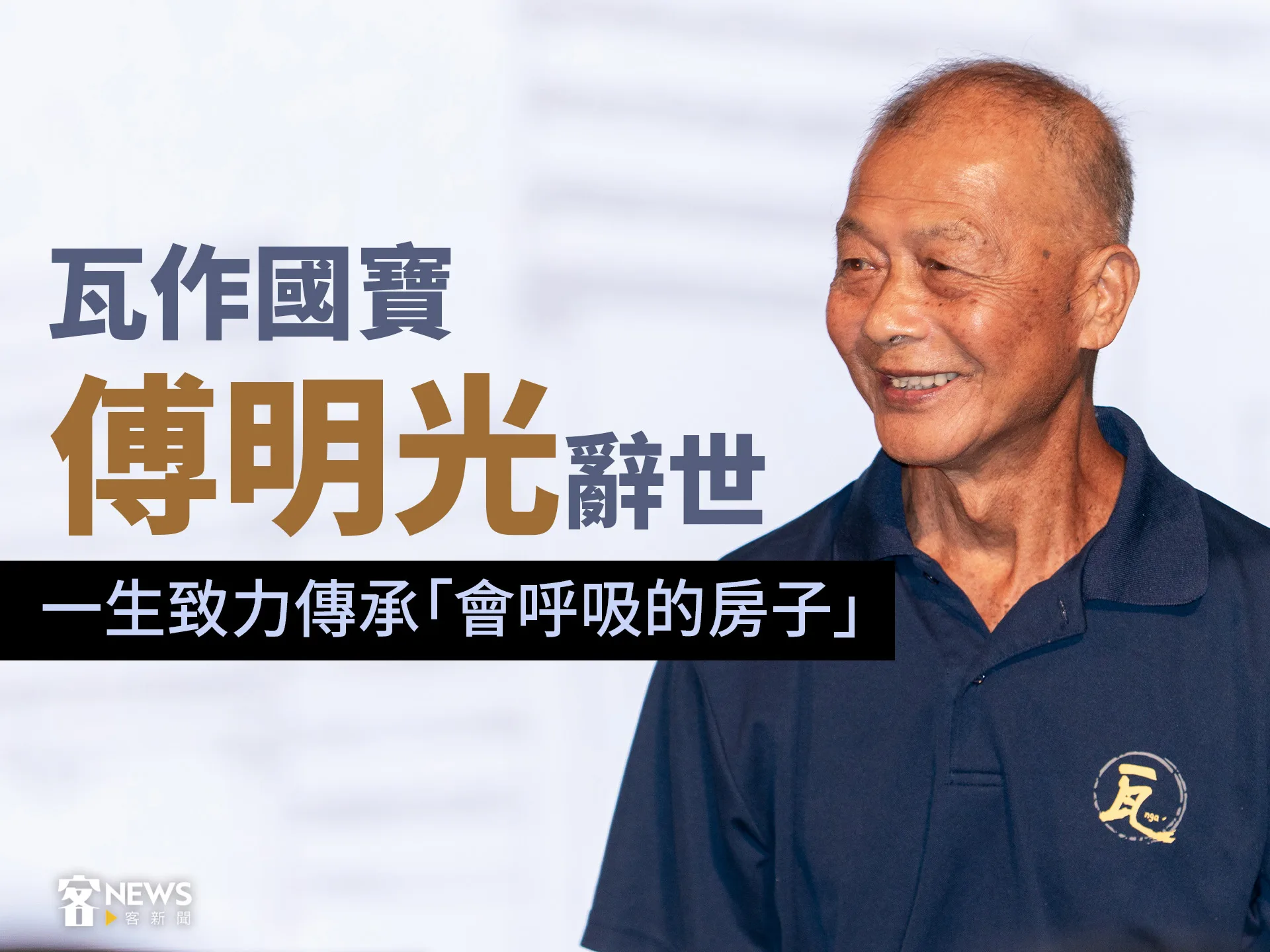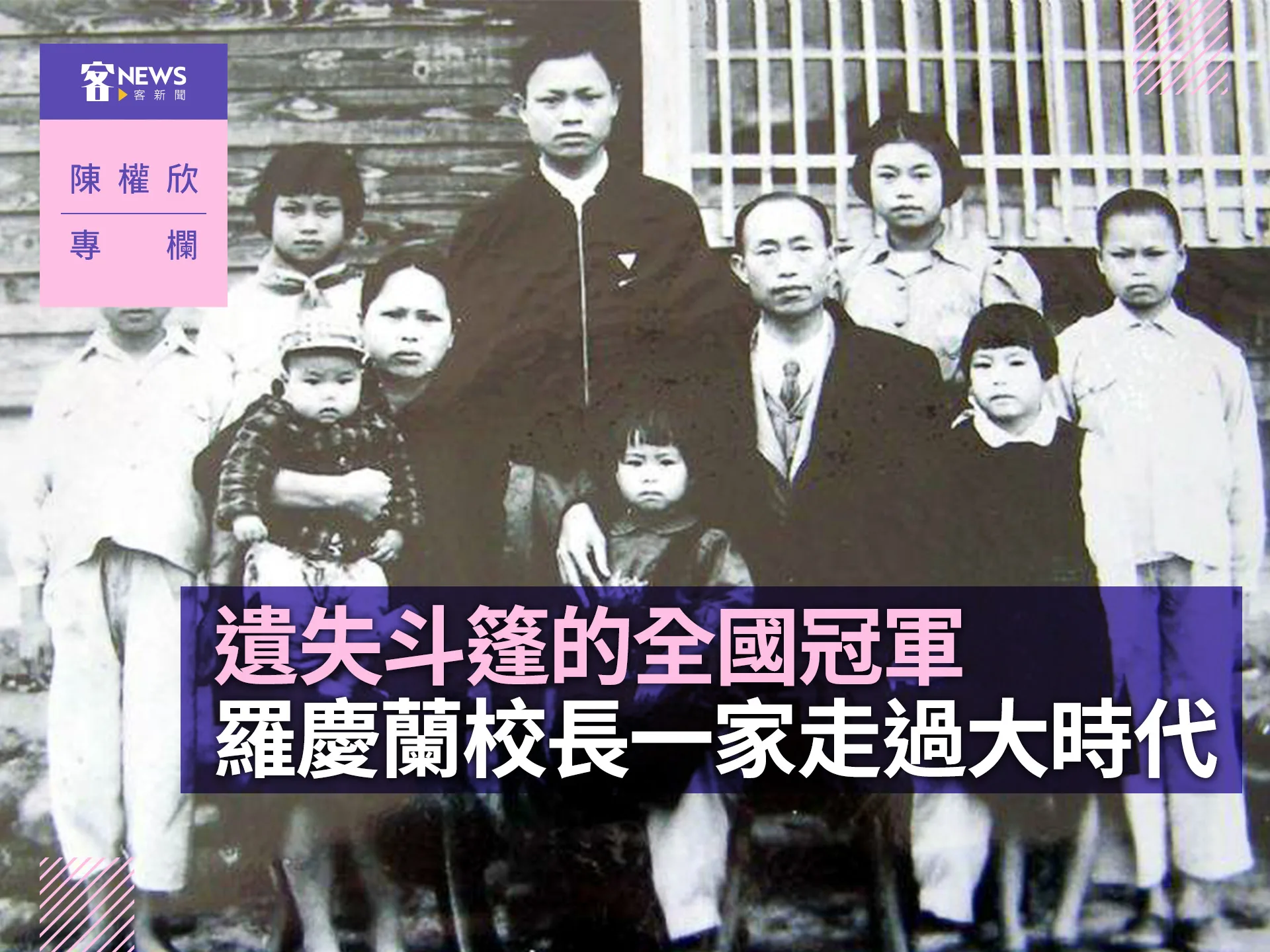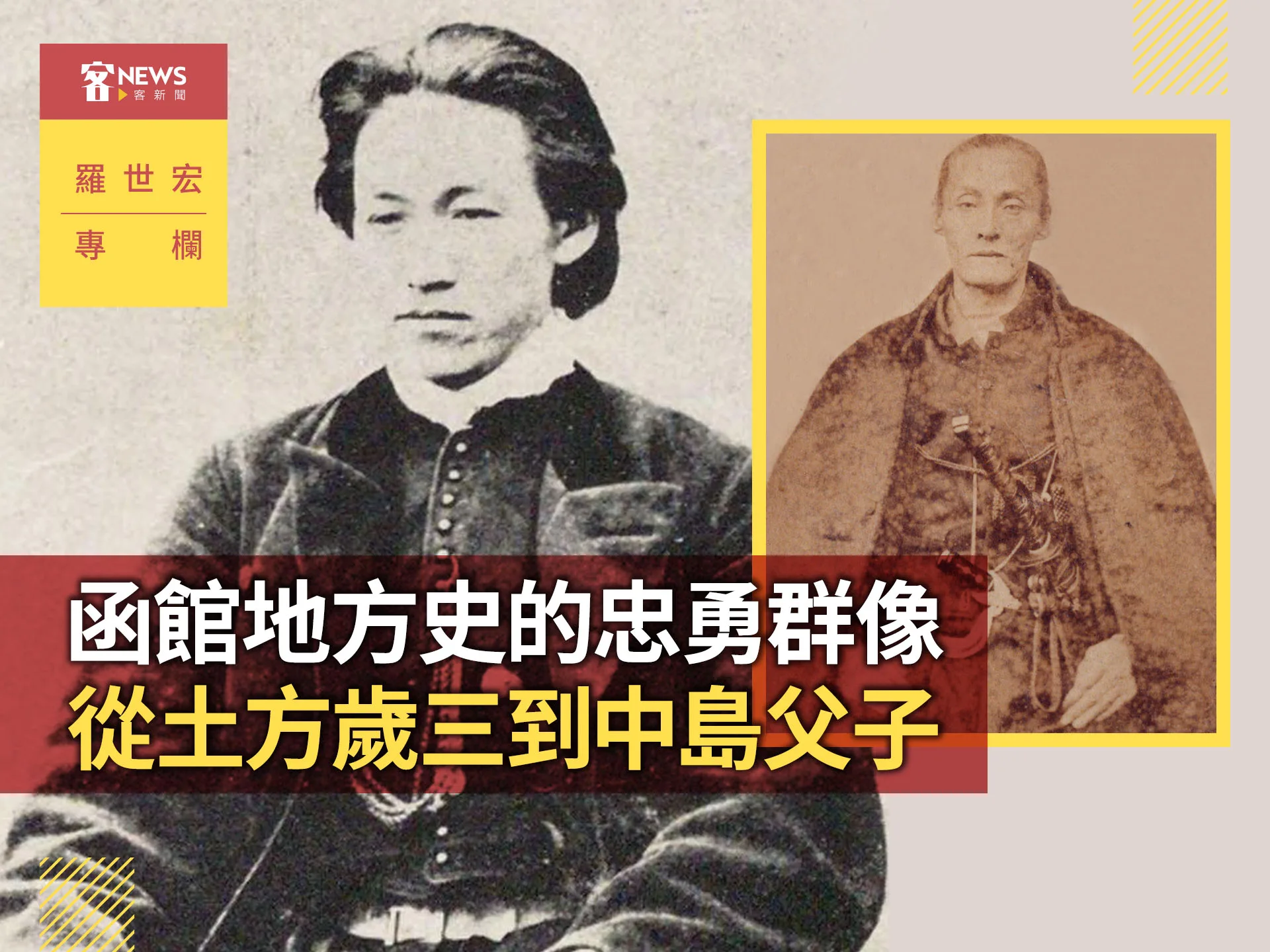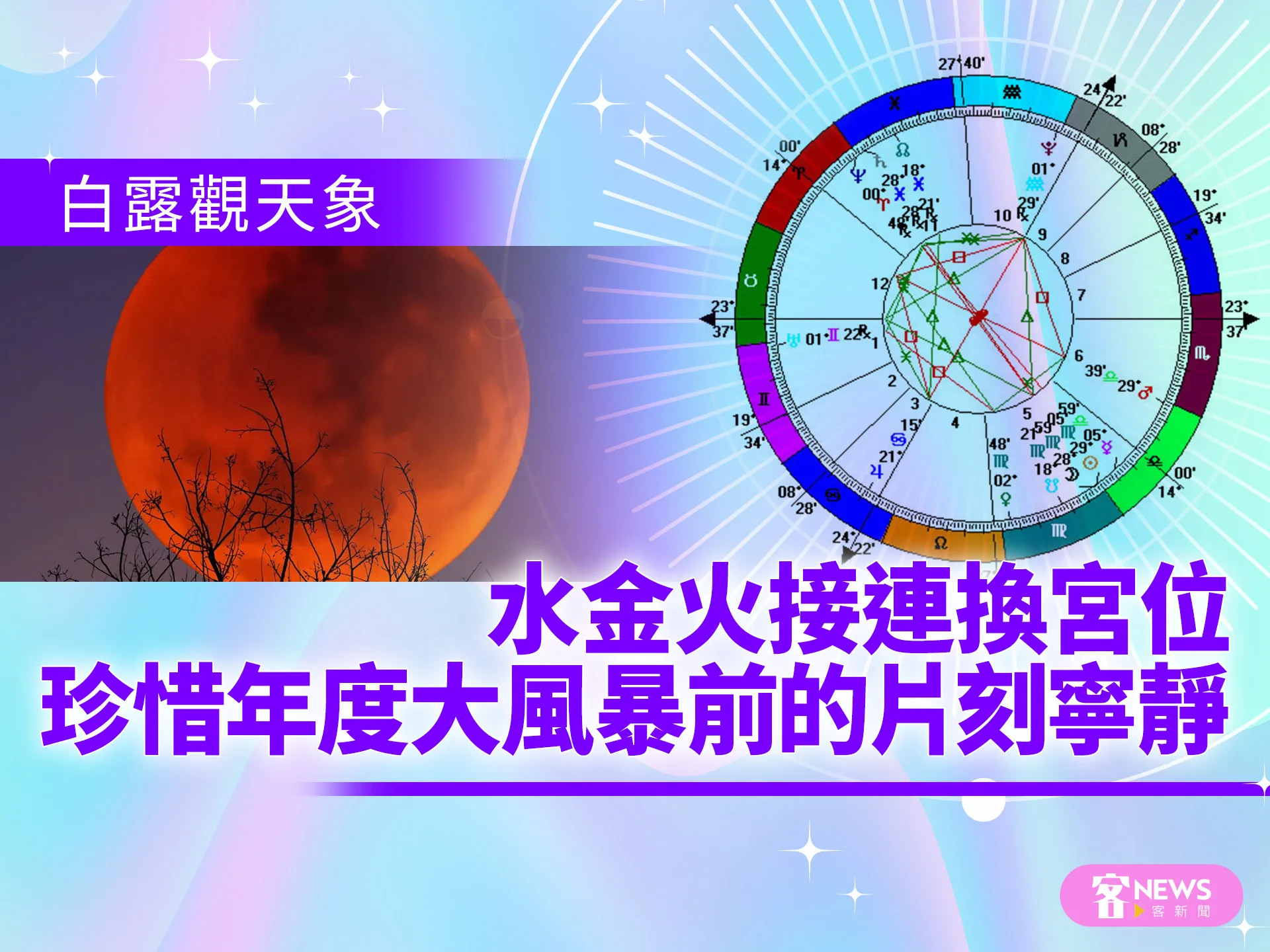文/蕭秀琴
曾任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作家暨譯者,著有《風物季語》、《料裡風土:往山裡去的地方,九種食材從山到海建構客家飲食》等書籍。現居離台北城約一個小時的小鎮,持續文字工作。
花生豆腐咬開一股熟悉感襲來,本來想整顆放進嘴裡,但客委會主委古秀妃和飲食考查大家蔡珠兒坐兩旁,萬一有個什麼實在不好看,畢竟聽過不知道多少則阿公、阿婆讓粢粑哽著(gangˊ doˊ,海陸腔)的災難性下場,尤其小時候噎著的感受從來沒忘過,然而我還是忍不住問了來自南客家的主委;「你們有沒有大粄圓,這個像不像?」她猛點頭,有像。
想來EMBERS的主廚郭庭瑋(Wes Guo)上山下海沒白忙,真有在味緒裡琢磨下功夫,客委會盤點客家食材讓精緻料理主廚做出新時代的客家料理,以這一段話幾個字就可以發展出上百篇論文;客家食材為何?客家人如何吃、如何料理,走到要面對氣候變遷大議題時間點,可以在誰的巧手上傳出台灣客家人的時代面貌。
「構樹擂茶與花生豆腐」是Wes端出的三道菜之一,另兩道是前菜「仙草蚵」,後一道主菜為「破布子奶油蒸魚」,從食材與料理上看都有被認為是客家的食材與食物——花生豆腐、仙草和用創造出台灣巧克力之光的南客可可豆漬破布子,讓雜魚有了精緻的氣韻。
席間蔡珠兒說,從我家出來走到這裡就可以看到三棵構樹,若不是聽過朋友抒發己志時提及啟發她在創作上運用在地元素的最初心念,是因為學生時代走在台大校園隨時可以看到構樹蹤跡,在台北市聽到這話還真新鮮,但仔細想想,我住的大稻埕慈聖宮四周小吃攤,邊喝魚湯邊百無聊賴的盯著構樹看的時候還真有,只是當時沒意會到那個是我在頭份家陽台上,不知道為什麼就冒出一棵長到探出頭的小樹。又席間此起彼落的「鹿仔樹」聲聲響,不管是台語還是客家話,大家對構樹呼喊鹿仔樹情有獨鍾。

用全台灣到處都是的構樹葉烘乾磨碎到粉狀,跟茶葉磨成抹茶粉大約差不多的樣貌,事實上,台灣客家認識擂茶是很晚近的事,追溯1980年代北埔發展觀光產業帶動的餐飲型態應該錯不了,中學時校外教學去北埔初認識這種玩法,念大學時輪到帶同學導遊客庄,甚至後來招待外國朋友認識客家,都還是同一家也是僅此一家茶店能擂茶。到如今擂茶和客家連結成「客家擂茶口味」是各大穀粉品牌訴求的在地健康選項牢不可破。
既是在短時間內擴散得如此迅速的族群印象,如何詮釋怎麼運用端看個人巧思,這道「構樹擂茶」看似主角其實是基底,功夫好就會有底蘊,真正讓人有感的會是在「花生豆腐」。
問六堆客家人都說花生豆腐從小吃到大,去外面吃板條可以順道吃,去菜市場可以買回家放冰箱,想吃就吃,說是吃了三、四代有百來年歷史,而我卻納悶,有歷史傳統的點心為什麼會叫「花生豆腐」而不是「番豆豆腐」?果然在客委會2011年發行的《內埔手感老智慧:發掘客家珍手藝》一書中就有,「以前東勢村有四到五位做番豆豆腐的師傅,番豆豆腐的製作技術也因東勢村人口外移而流傳出去。」真正是傳了三四代有歷史源流的名菜,要變化手法就要經得起考驗。

關於料理創新我經常會想起日本時代江山樓主人吳江山詮釋台灣料理與中華料理的不同,他在〈臺灣料理の話〉中闡述過,「名廚作法的變化就像為政者施政的變化。」花生豆腐並不是加了花生的豆腐,而是客家米食的一種,一種客家婦女為了解決過剩食材或在燥熱豔陽下為了安撫小孩發明的點心,一如長久以來把在來米拿來浸泡、磨漿再蒸熟,而這道摻曬了好幾天的番豆或許是為了保存熱力,蒸好擱在放豆腐的木盒裡放涼,一道名點誕生。
Wes的花生豆腐用蓬萊米取代在來米,沒放在模型裡蒸,搓成糰子,把魷魚乾、白玉蝸牛等配料如煏配頭或客家小炒般爆香包進去挼大粄圓,這是三道菜中最接近傳統客家味緒,讓鄉親不須言傳就能會心一笑的料理。
同類是一種微妙的心領神會,不一定需要具體的形象就能識別,在台北搭計程車從沒錯過客家鄉親語音動作,走過世界五大都會,絕對不會錯把港女當作台灣妹,沒有凍感的「仙草蚵」就像阿婆的燒仙草放涼後早已不知蹤跡,南客的「對面烏」北上被叫成「爛布子」,都不知道這麼多子怎麼煎蛋,抑或說該如何把子去掉,若是我爸一定會問,要用手指把子去掉的嗎?若為是,我想他會有一股衝動想沖水洗一洗。
客家食材與客家菜的時代面貌,需要被反覆驗證也必須不斷翻新手法,才可以變成能日日操持端上桌的家常,也才會被冠以客家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