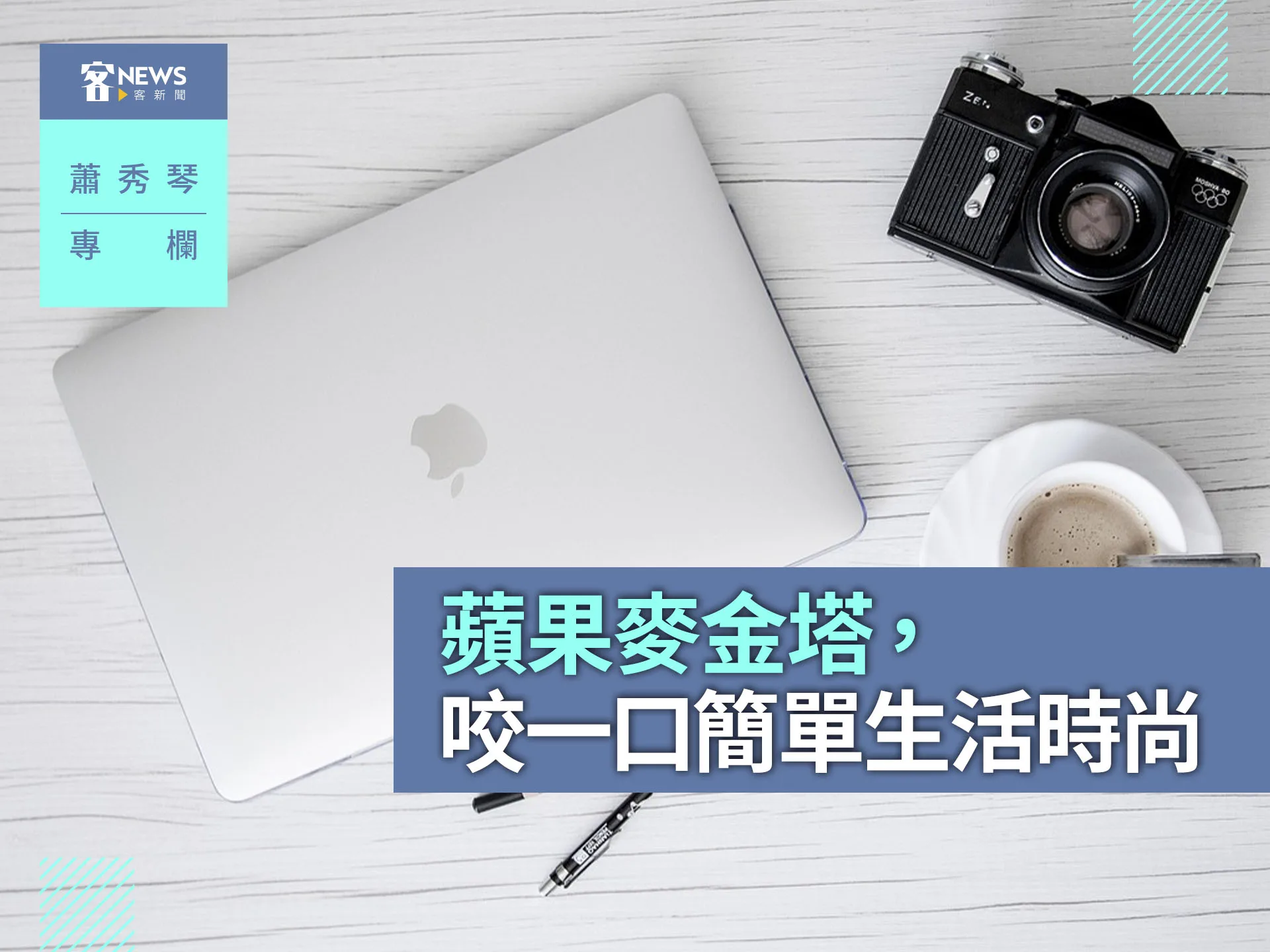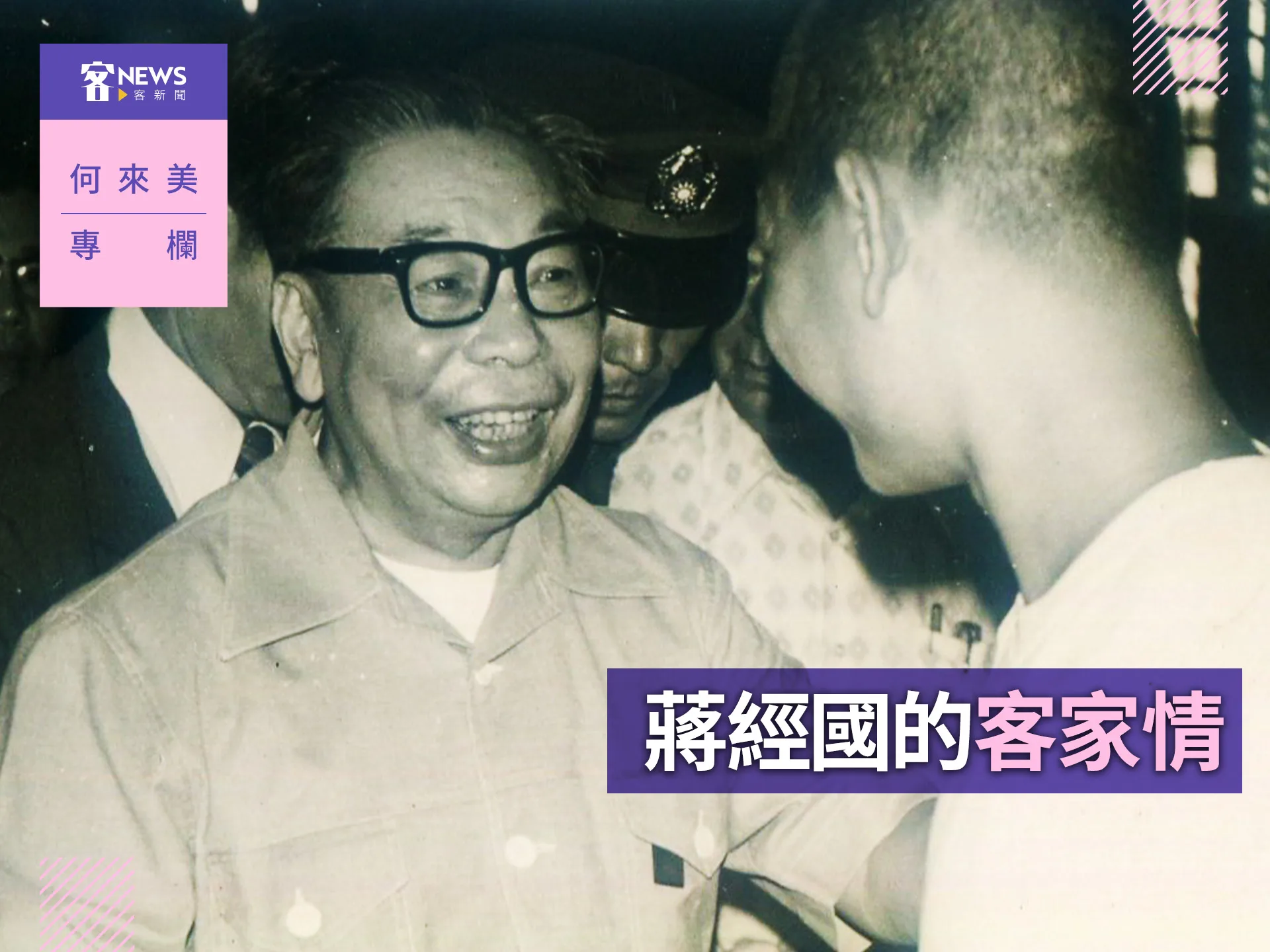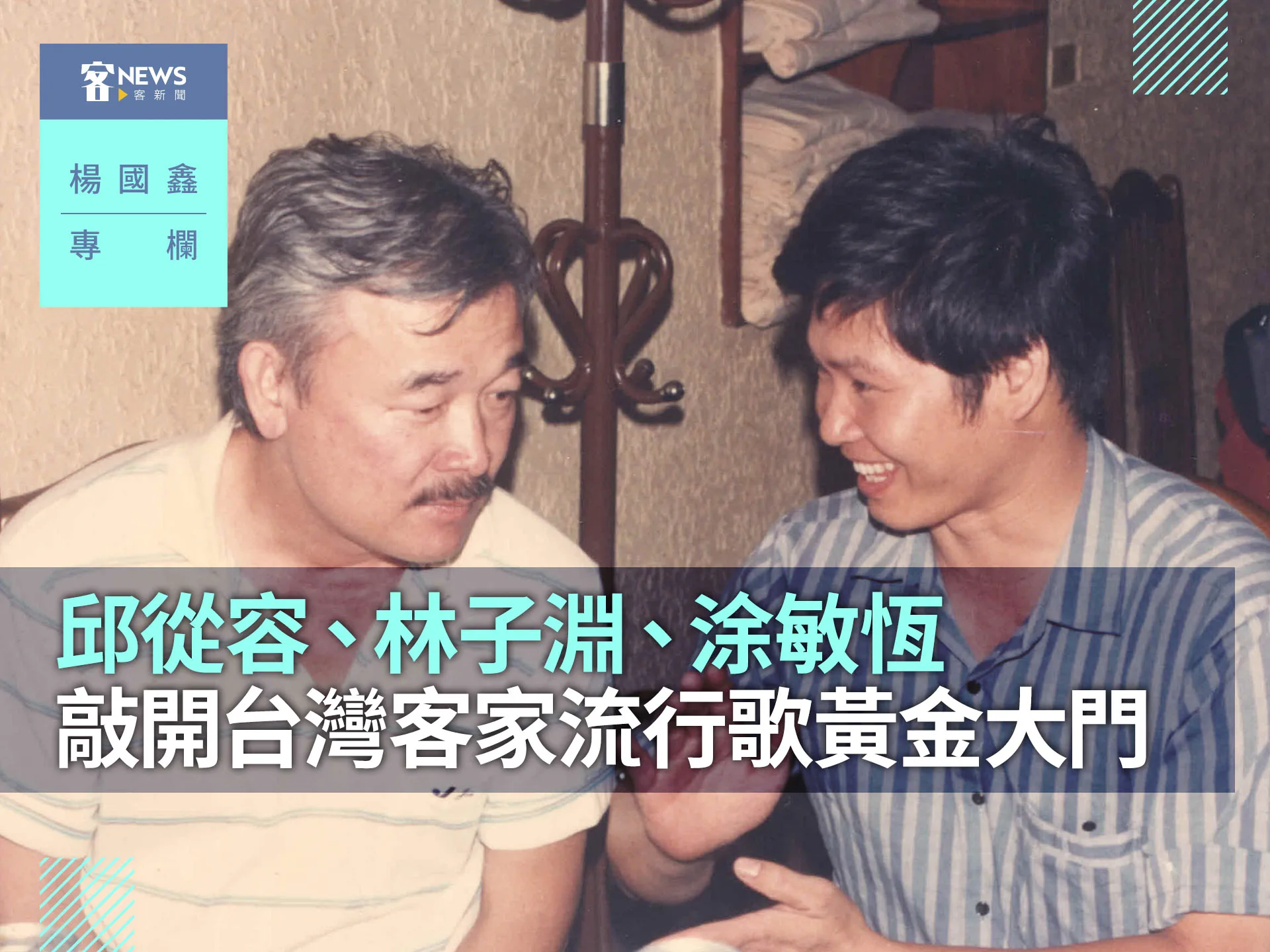文/蕭秀琴
曾任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作家暨譯者,著有《料裡風土:往山裡去的地方,九種食材從山到海建構客家飲食》、《料理臺灣:從現代性到在地化,澎湃百年的一桌好菜》等書籍。現居離台北城約一個小時的小鎮,持續文字工作。
春天繞山花哪裡去,淺山丘陵彎彎繞繞總是容易往山裡去,賽夏族人說,跟著蜜蜂走是採集與狩獵的地方,豐饒景象渲染大地山色,南庄東河瓦祿部落是賽夏語walo’,是蜜蜂也是蜂蜜,河岸上吊橋前有座瓦祿產業文化館,1924(大正13年)年當地人集資168日圓,建造東河派出所直到 1988 年遷出,現今的瓦祿產業文化館是東河社區在921 災後重建的地方創生基地。
人類吃蜂蜜有將近1萬年的歷史,比喝葡萄酒的歷史來得長,希臘神話裡的酒神戴奧尼索斯,先是蜂蜜酒神才成為葡萄酒神,蜜蜂是諸多原住民的創世神話傳說,蜜蜂跟人類相依存,有蜜蜂傳授花粉的地方才有生命的存在,這是現代環境生態學的基本常識。
最早發現台灣原住民蜜蜂語源一致性的博物學家鹿野忠雄採集到的、跟蜜蜂有關的字源有;魯凱族稱作valro和賽夏語說walo’近似,太魯閣跟奇萊雅語同樣說walu,而布農語稱作vano、蜂窩是asang 亦為部落、家鄉的意思,布農族更細分出胡蜂是pakozizialu,最有趣的是排灣族語雄蜂是maziyaji,雌蜂為taiinan,甚至能分出熊蜂或木蜂都叫做pagchiu,由此確定以山林維生的原住民很早便會分辨雌蜂與雄蜂及其特質,用來確認採集蜂蜜,甚至飼育蜜蜂食用蜜。

自日本時代起就是旅遊勝地的關子嶺,日本人稱此為台灣第一的養蜂地,這一區的在地人傳統的養蜂方式為吊掛在屋簷下的蜂窩裡,有一群一群的野生蜜蜂繁衍,年復一年甜嘴,研究人員保守估計,此地原漢交流養蜂技術至少三百年。
希臘神話裡,蜂蜜是奧林帕斯山上眾神賞賜滴落人間的仙露(Nectaar),包藏在花心裡為花蜜,引蜂吸啜為蜂蜜,客家人說蜂糖(pungˋ tong,海陸腔)是櫥櫃裡常備的食糧,習以為常喝蜂蜜水,或許是從前只有漢藥的時代,加在湯藥裡比較不苦,直到今天漢藥製丸仍然以蜂蜜為引做為凝結媒介。
小學校外教學到最遠的山裡向天湖,森林裡一箱一箱的蜂箱佈滿森林,幸運的話可以看見養蜂人取蜜,煙燻陣陣好似看撮把戲(cod baˊhiˇ,海陸腔)變魔術,長大一點自以為是南庄名產桂花蜜就在此,原來根本不是一回事,桂花恰恰是沒有花粉讓蜜蜂採的一種花,桂花蜜是桂花加蜂蜜或是桂花和麥芽糖加在一起的糖蜜。
不論是向天湖還是蓬萊森林裡的蜂蜜是為森林蜜,在還沒有被珍視前就如珠玉般存在的事物,如今森林蜜備受重視源於2017年,在台灣人還沒有被covid-19肆虐之前,稱作東方蜂的台灣原生種野蜂就先被中國偷渡進來的「東方囊狀病毒」殘害一度幾近滅絕,在學界和業界聯手逐漸平息後,最先在於中高海山林地帶,蜂群逐漸回來,野蜂能適應較低溫採集森林裡繁多蜜源植物的特性,成為「森林蜜」的蜂種。
另一種原本接近消失的原生種無螫蜂,只有蒼蠅般大小,沒有蜂針,不會螫人,holo語叫雨神蜂,在計畫性飼育下也逐漸回來,日本時代調查到台灣有八種無螫峰,是原住民飼養最重要的授粉昆蟲,現今只剩下黃紋無螫蜂(Trigona ventralis hoozana),是能生產蜂膠的抗發炎物質,感冒過敏滴一滴蜂膠紓緩症狀。
能在高海拔地區生存的台灣原生種蜂,是森林生態良窳的見證者,而人們也能透過吃蜂蜜來認識森林與植物,吃蜜成了風土飲食,一直以來台灣人認為最好的蜂蜜為龍眼蜜,殊不知一處天然林可能有上百種植物,包含木本、草本等各種開花植物,有些純林更可以標榜特殊性,像是八仙山的台灣土肉桂,或是中部山區的大頭茶,一般來說,蜜蜂覓食範圍約3公里,若在山谷則約2至2.5公里,確實可以彰顯森林植物的特質,標明植物的森林蜜最能見證風土與生態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