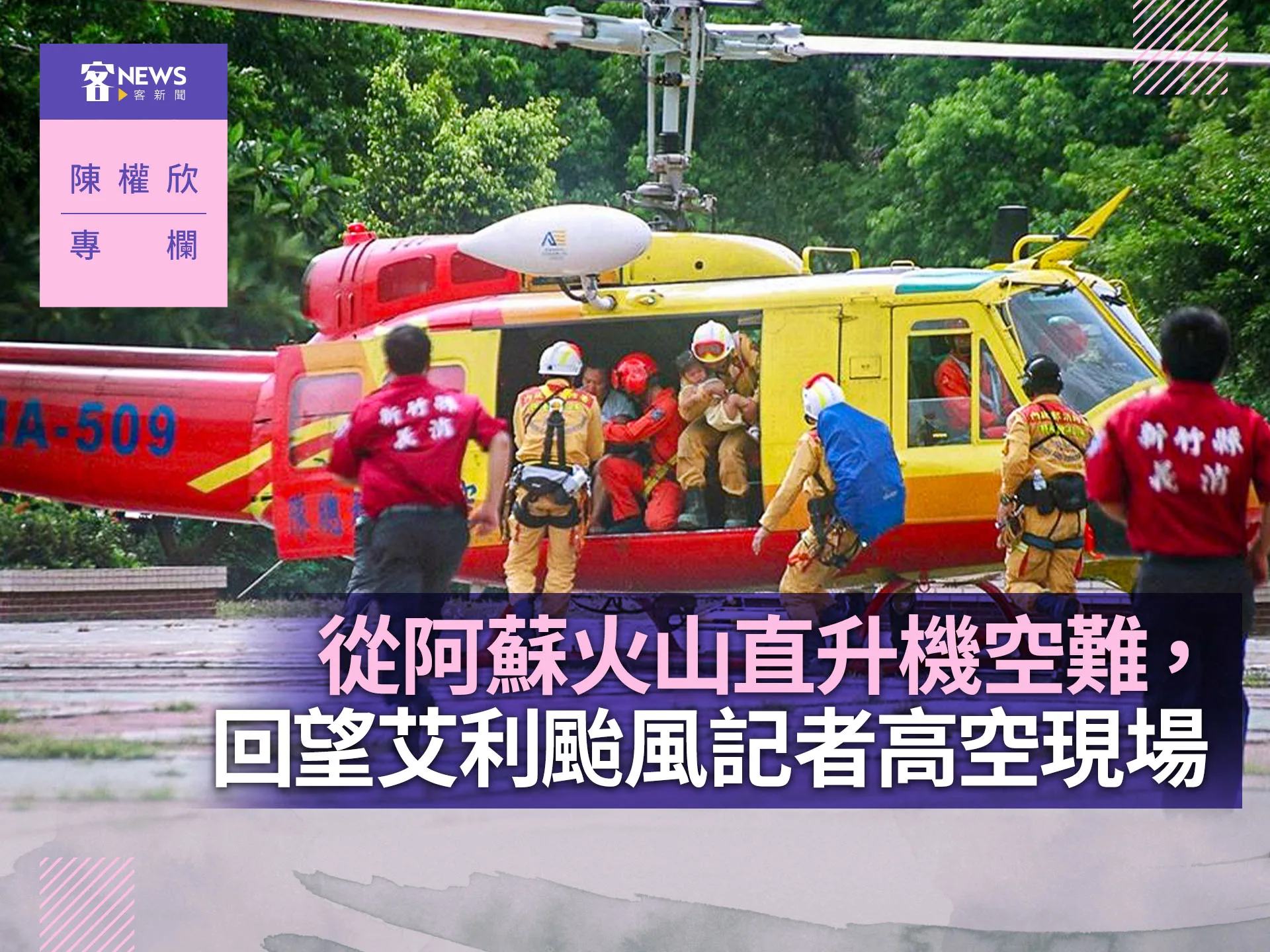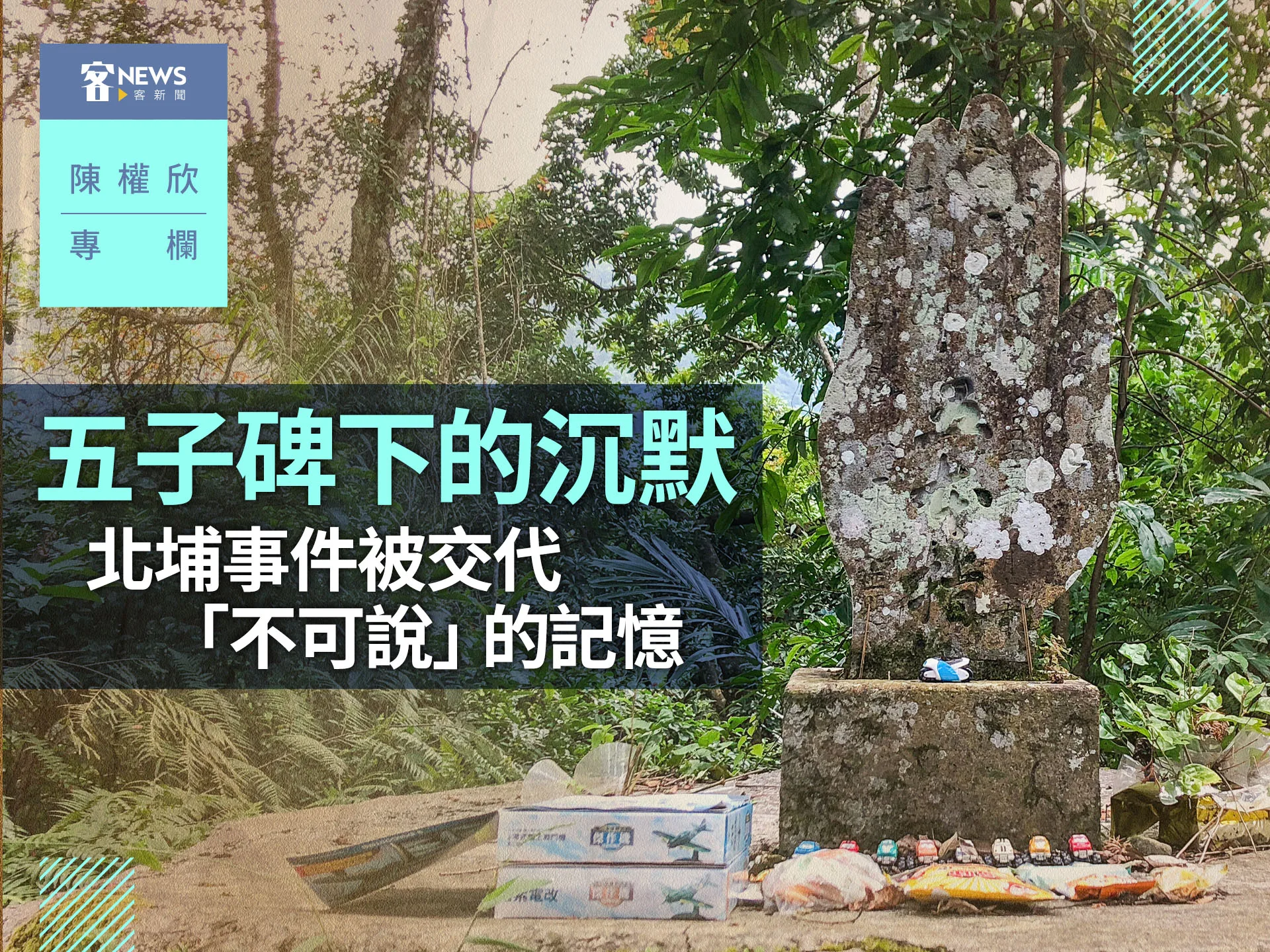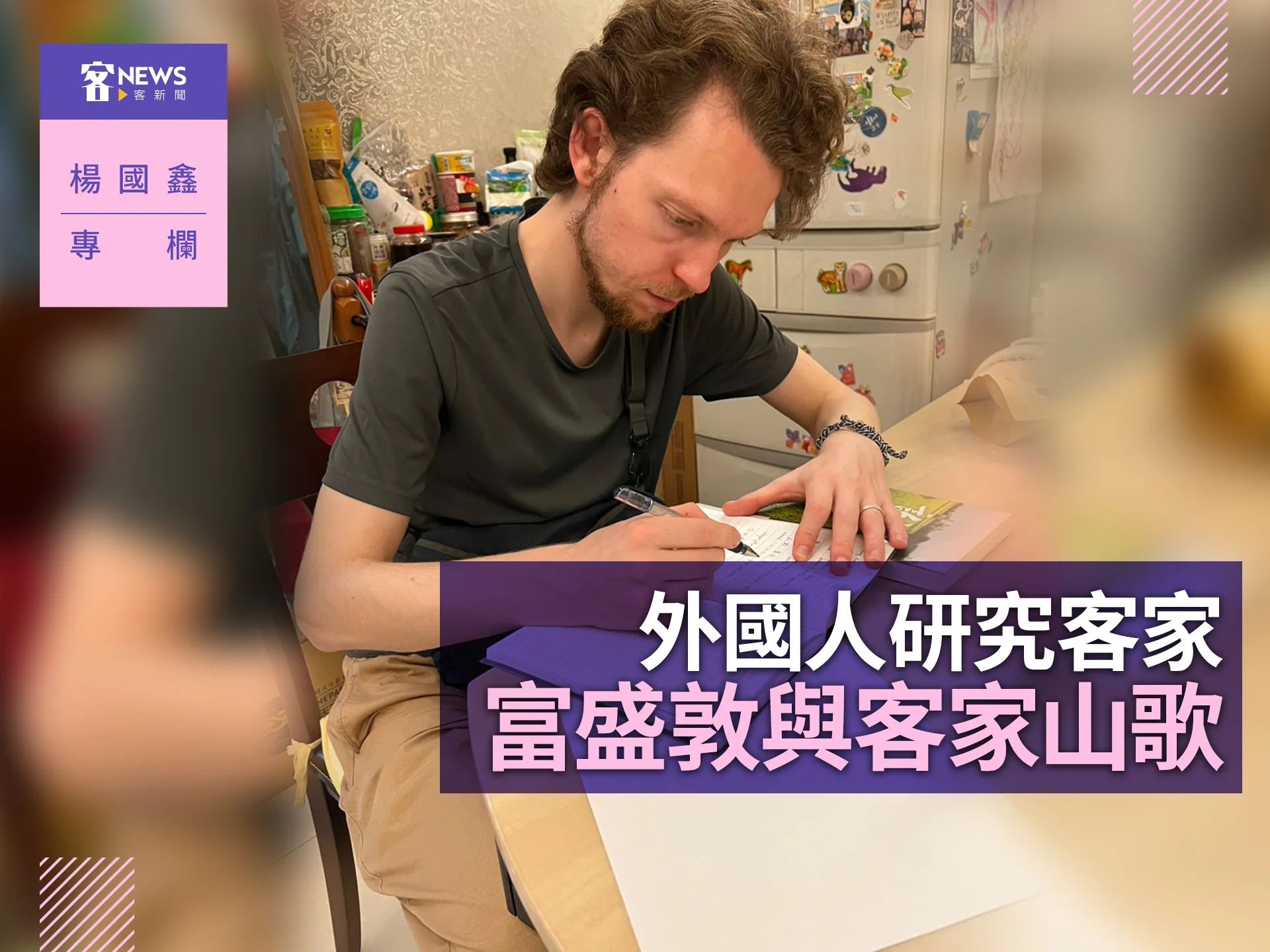文/蕭秀琴
曾任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作家暨譯者,著有《料裡風土:往山裡去的地方,九種食材從山到海建構客家飲食》、《料理臺灣:從現代性到在地化,澎湃百年的一桌好菜》等書籍。現居離台北城約一個小時的小鎮,持續文字工作。
凱道上排滿的橘色大抱枕讓人好想抱回家,胖胖圓圓的柿子造型罐好想要一個,圖個事事如意好事連連來,柿子的外型討喜,橘色溫暖,綠色蒂頭一點綴就亮了起來,不管是設計師還是一般人,有誰會不喜歡這個吉祥物。
但這些都不是客家人熱愛的柿子,有人喜歡紅柿仔(fung ki+ er,海陸腔)軟甜滋味像冰淇淋又像粢粑,就是挑個軟柿子吸。嗜食者等著水柿仔脆又甜,我愛沙沙的口感咬起來咖-咖-咖的好脆;柿子自來就是喜慶的象徵,客家米食有一款粄叫假柿子,跟發粄一樣,都是蒸起來會裂紋開花,吉祥富貴好敬神,吃起來蓬鬆甜滋滋好歡喜。
假柿子用在來米磨漿壓乾變成粄脆(米漿團),再加上砂糖或烏糖、酵母或老麵,靜置發酵後搓成一團一團,成功發酵的粄團,蒸起來裂紋如柿討喜,吃起來軟糯口齒生津如阿婆愛的紅柿子,所以叫假柿子。柿用海陸腔發音ki跟漢字的「喜」最為相像,四縣發cii像「吃」也很有意思,吃個柿子吃喜氣,無論如何都是好事一樁。


柿子分澀柿與甜柿,台灣本地種的傳統柿子多為澀柿,大家較為熟悉的澀柿有牛心柿、四周柿、石柿和筆柿,必須脫澀後才能上市販售,自家庭園種的柿子亦然,因此,傳承柿子脫澀技術成為主婦的手藝技能,流傳的故事、秘方成為傳頌一時的典故。因此,客語發展出柿嫲(敲碎發酵的柿子)浸柿仔成為脆口的水柿仔。
柿仔富含大量可溶性單寧(Tannin),澀味濃重也難以消化,脫澀是人類飲食發展出來的食材處理技術,方法是將果實隔絕空氣,把可溶性單寧變成不可溶性,果肉纖維軟化,熟成的果實才會釋放糖分散發香氣,並且不是所有的果實都有幸能在叢紅,照片裡,在秋風中晃蕩的紅柿子多為甜柿,即便是甜柿也要裝袋防蟲防小動物啃食,才得收穫。
浸柿仔於客家人,一直以來都有口耳相傳的純天然做法,只是工序繁複需要耐心,因此多為自家食用或小量生產,善於製作食材的客家阿姆,會將採下來的柿子放在桶子裡浸水,拿三四顆柿子敲碎後一起泡約一個星期,時間長但安全,熟巧的人能夠辨識需不需要換水或會不會泡過頭而腐爛。但做來買賣需要量產的做法,通常以電石/土燜熟,電石主要成份為炭化鈣,過程容易傷害眼睛或肺部等有礙健康,並且靠近電石的柿子會受傷變黑不討喜。
曾經三斤一百都嫌貴的的水柿仔,如今和精品的富有甜柿一般成了高價水果,一斤八十元在市場中都難以找到;追根究底不外老樹乏人照料成了果園裡裝飾性樹木,即使能收成也找不到會浸柿脫澀的手藝,想吃顆水柿子還得先問問誰會傳統手藝,說起來無恁該食(mo anˇ goiˋ shidˋ,海陸腔)之不容易啊,代誌毋是憨人想的遐爾簡單(holo與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