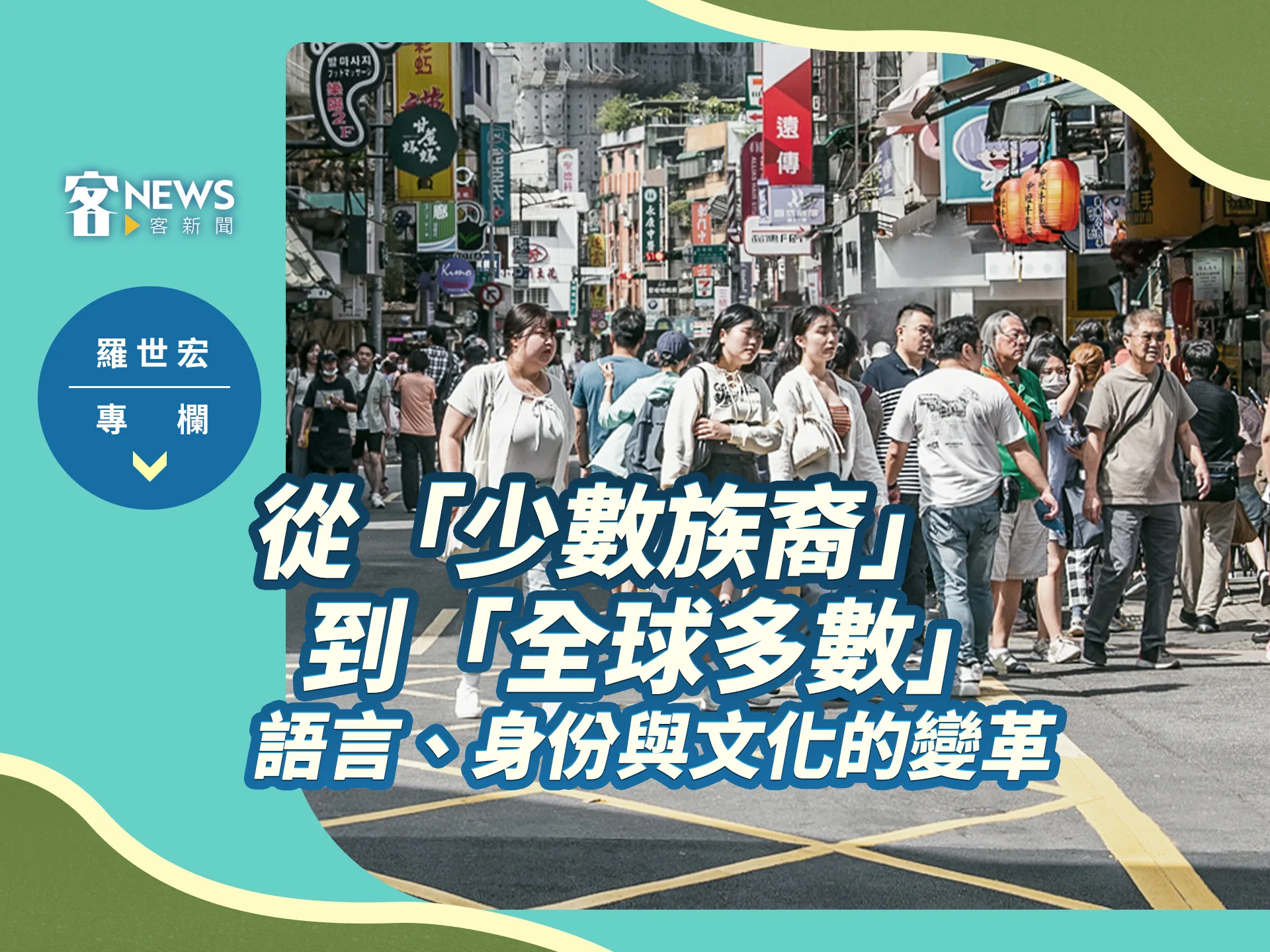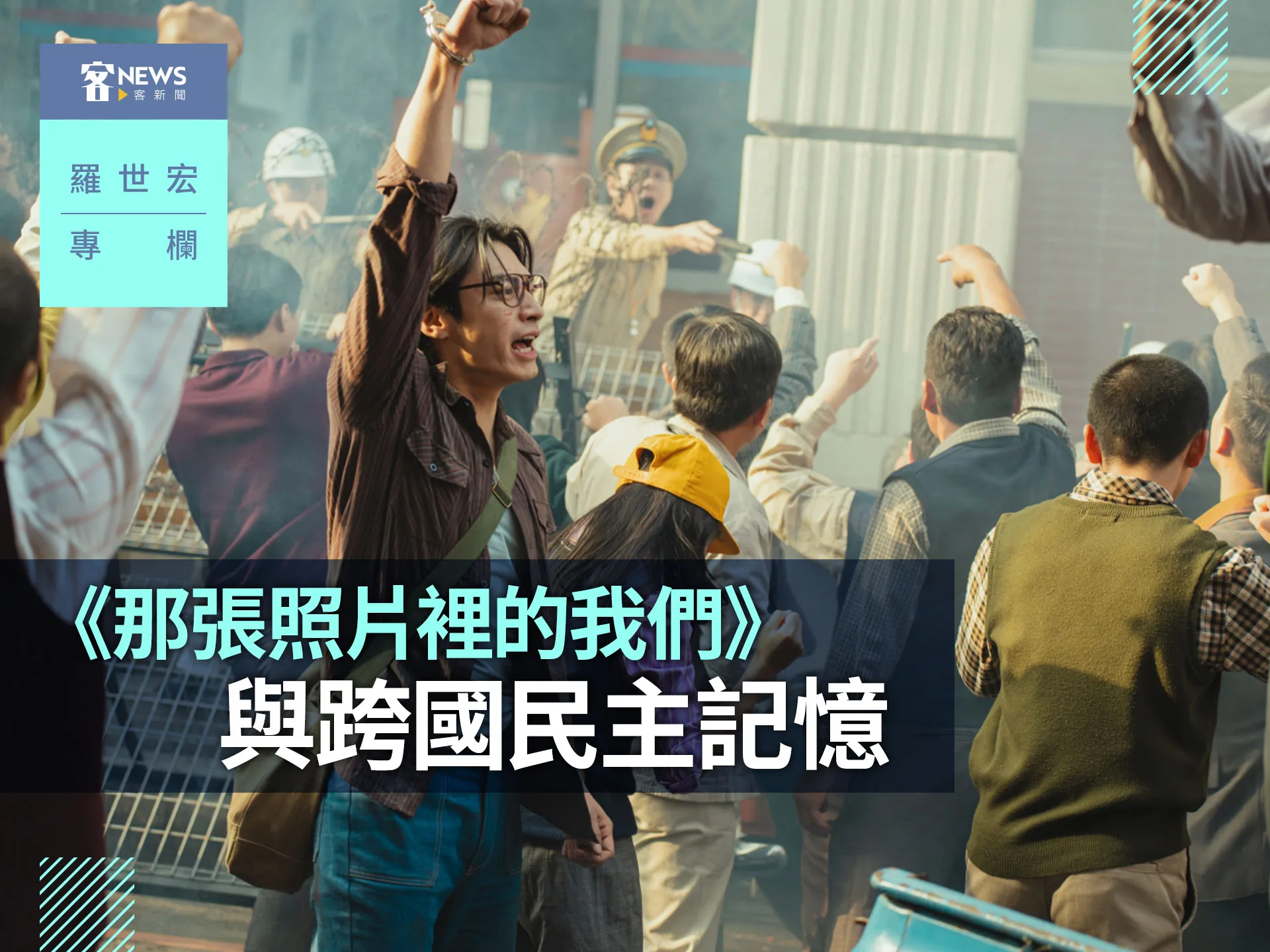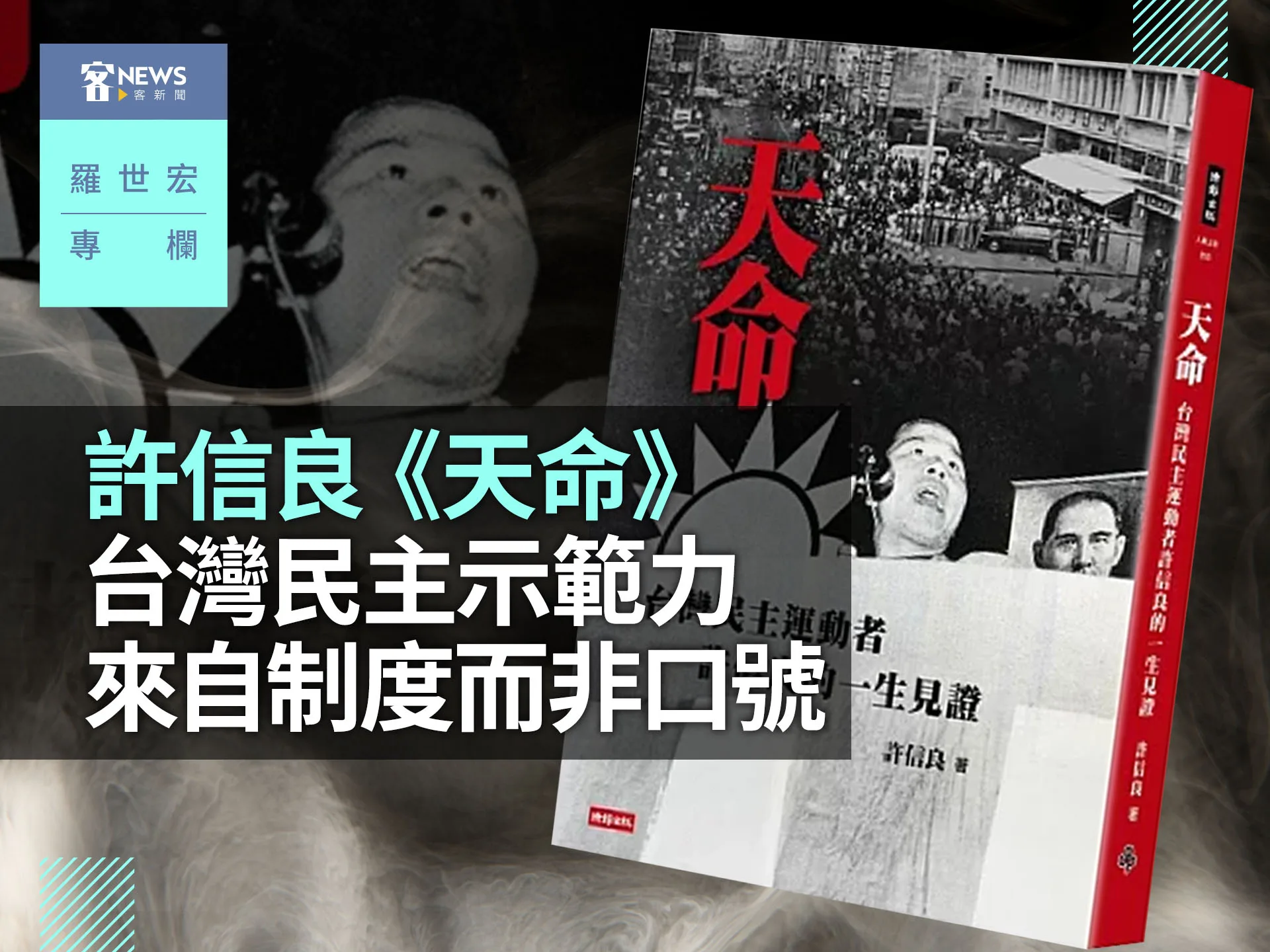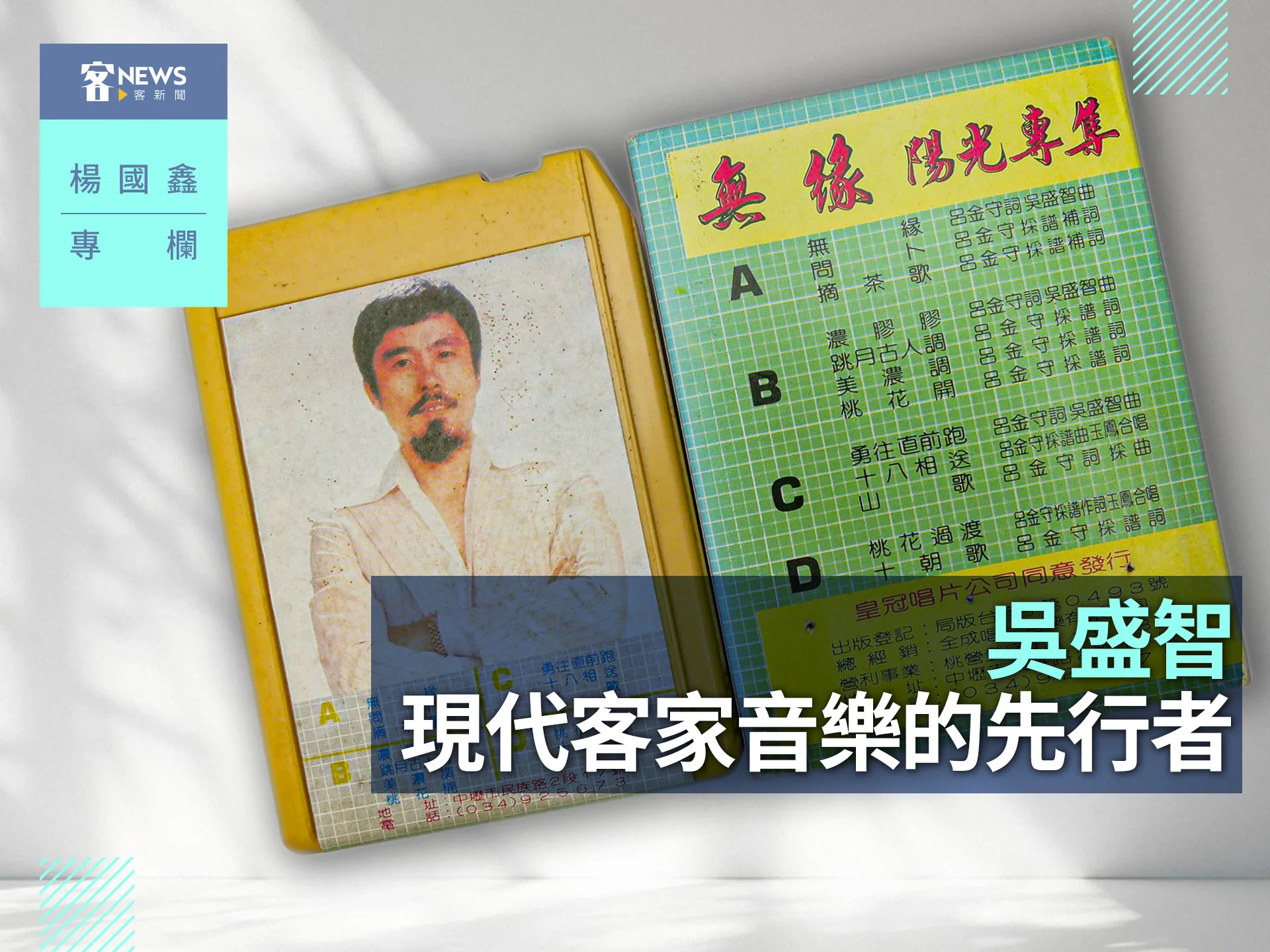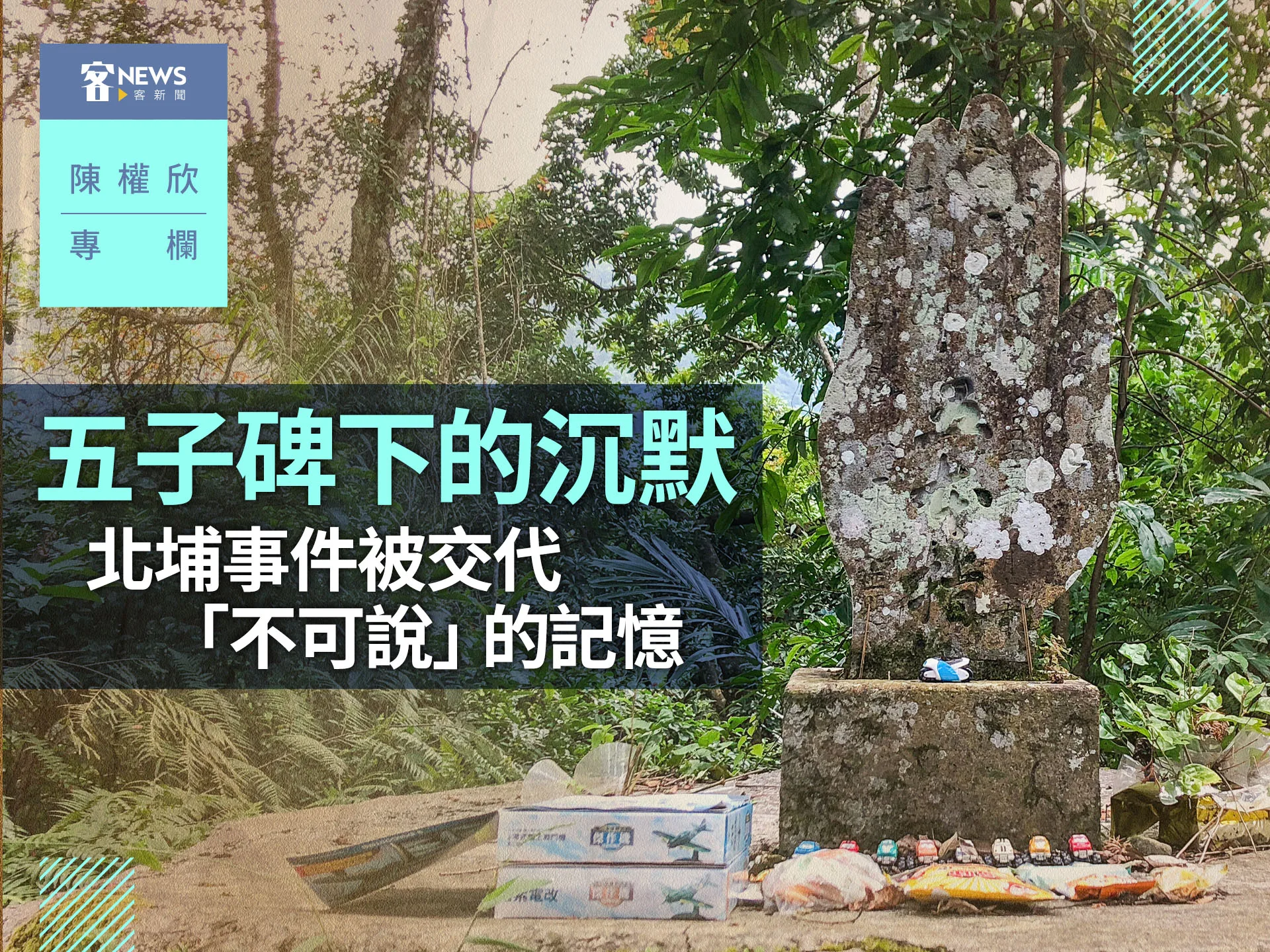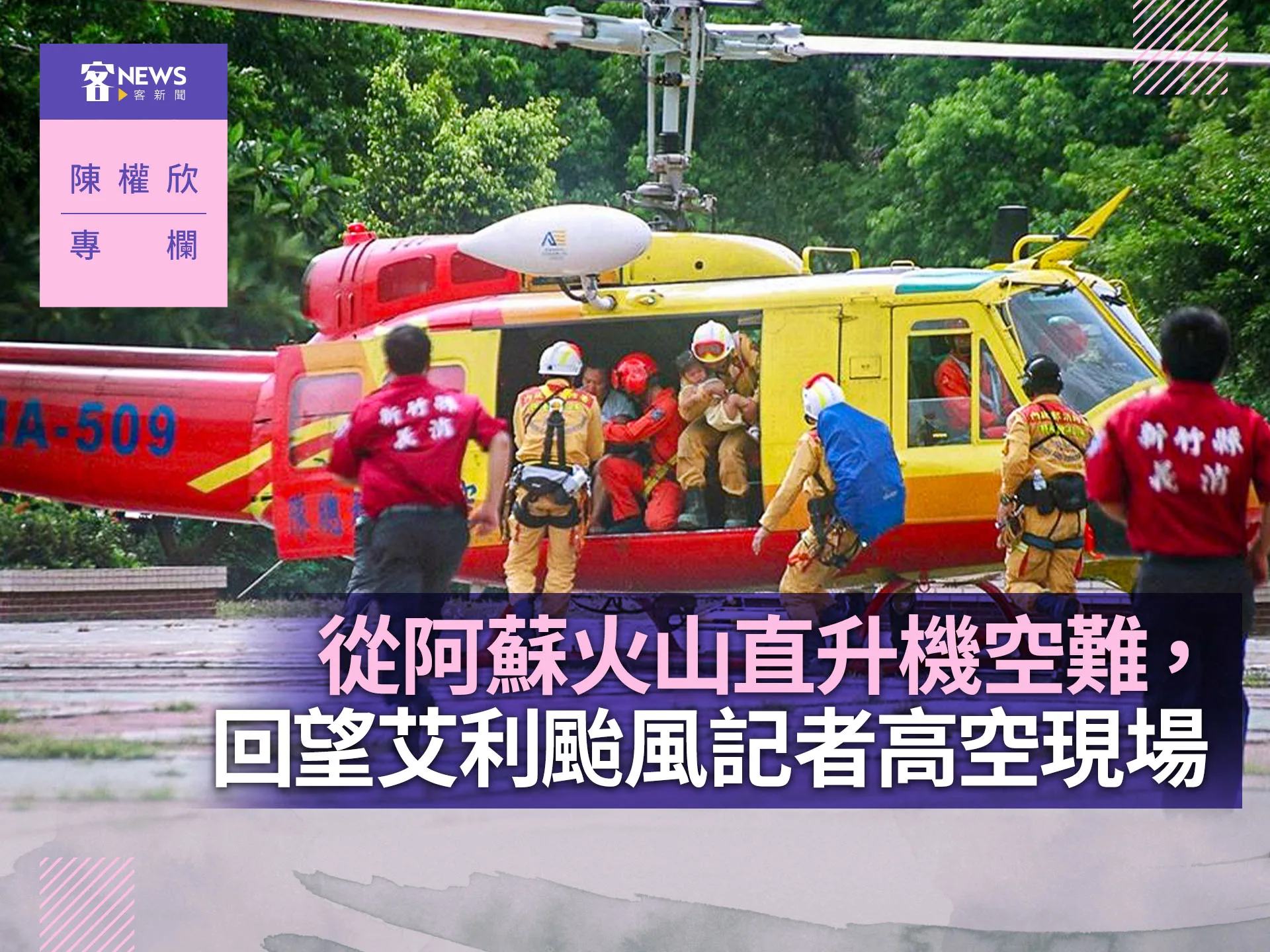文/羅世宏(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的缺點是「好為人師」。目前持續關注傳播政策、平台問責、中國傳媒、新聞業永續發展與數位轉型、和平新聞學(peace journalism)、氣候新聞學(climate journalism)及人工智慧(AI)等研究主題。
近年來,關於族群的稱呼成為全球焦點。過去常被用來泛指非白人的「少數族裔」(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黑人、亞裔及其他少數族裔的縮寫)一詞逐漸被淘汰,而「全球多數」(People of the Global Majority)這一新詞正快速崛起,強調全球80%的非白人族群,目的是為了翻轉過去非白人被視為「少數」的觀念,並重塑多元平等的身份認同與族群關係。
根據BBC報導,倡議者認為「全球多數」一詞有助於重新定義非白人群體的身份。一位威爾斯的族群平等倡議者唐娜·阿里指出,這個詞讓非白人感受到更多力量和團結感,讓他們擺脫「次等」的標籤,認識到自己在人口數量上的優勢。然而,這種統一的稱呼也存在問題:它忽略了非白人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可能過於簡化,甚至加劇族群間「我們」與「他們」的對立。
學者達倫·切蒂也認為,雖然「全球多數」能讓人們重新認識全球非白人群體的數量優勢,但這個詞彙過於籠統,無法捕捉族群內部的複雜性。把非白人群體統一為一個單一身份,可能忽略了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與獨特性。
影響所及,「BAME」一詞近年來已逐漸被「全球多數」一詞所取代。英國媒體如BBC與第四頻道已停用「少數族裔」一詞,認為它過於籠統,忽視族群的多樣性,而且無法準確反映各個族群的真實經驗。同樣地,英國政府也在2022年宣布不再使用「BAME」一詞來統稱所有非白人群體,轉而使用更加精確的稱呼。
這一用語的變化,反映了社會對於語言和代表性的反思。將不同族群過於簡化地整合在一個詞彙中,往往無法充分代表他們的獨特性。以「BAME」為例,它包括黑人、亞洲人及其他少數族裔,忽視了這些族群之間在文化、背景和經歷上的重大差異。
娛樂產業的變革也對這場語言之辯起到了推動作用。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BAFTA)為回應對其多樣性不足的批評而有所改革,並且開始放棄使用「BAME」一詞,改用更具體的族群名稱。
「全球多數」這個新的泛稱,顯示了語言在重塑族群身份的影響力,但這種力量也有其局限。例如,語言的改變不能完全解決現實中的不平等問題。達倫·切蒂強調,語言使用應基於具體情境和目標來決定。例如,「全球多數」此一用語在全球層面可能適切,但在某些國家如英國或美國,由於非白人群體仍然是人口中的少數,「全球多數」的稱呼在這些國家似乎顯得有點與現實脫節。
無論如何,具族群平等意識的用語改變,確實有其正面意義,但真正的平等還需要超越語言。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語言的變革,更需要制度和結構上的改革,最終達成消除族群偏見的目標,讓所有人以平等身份相互理解、尊重與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