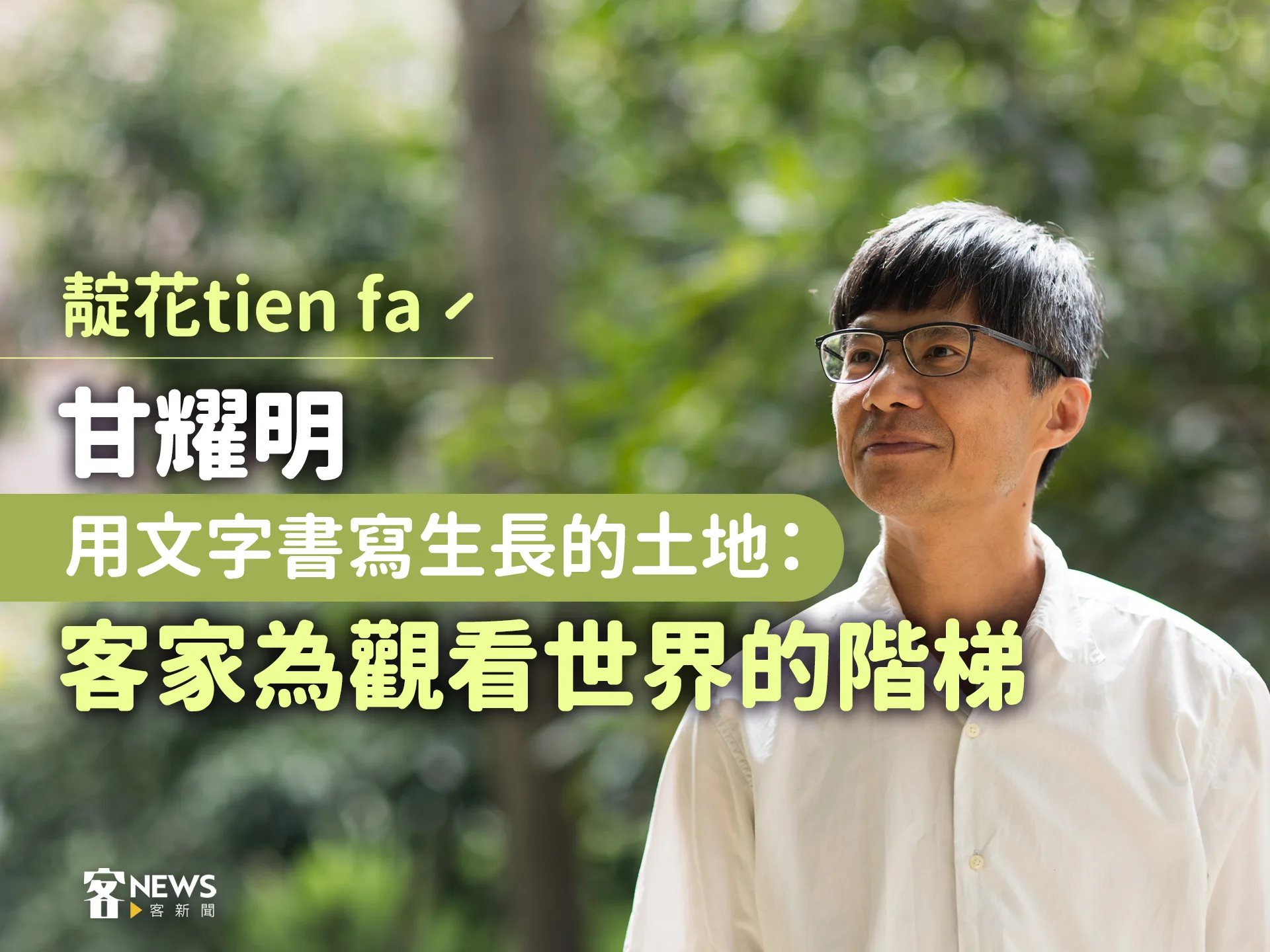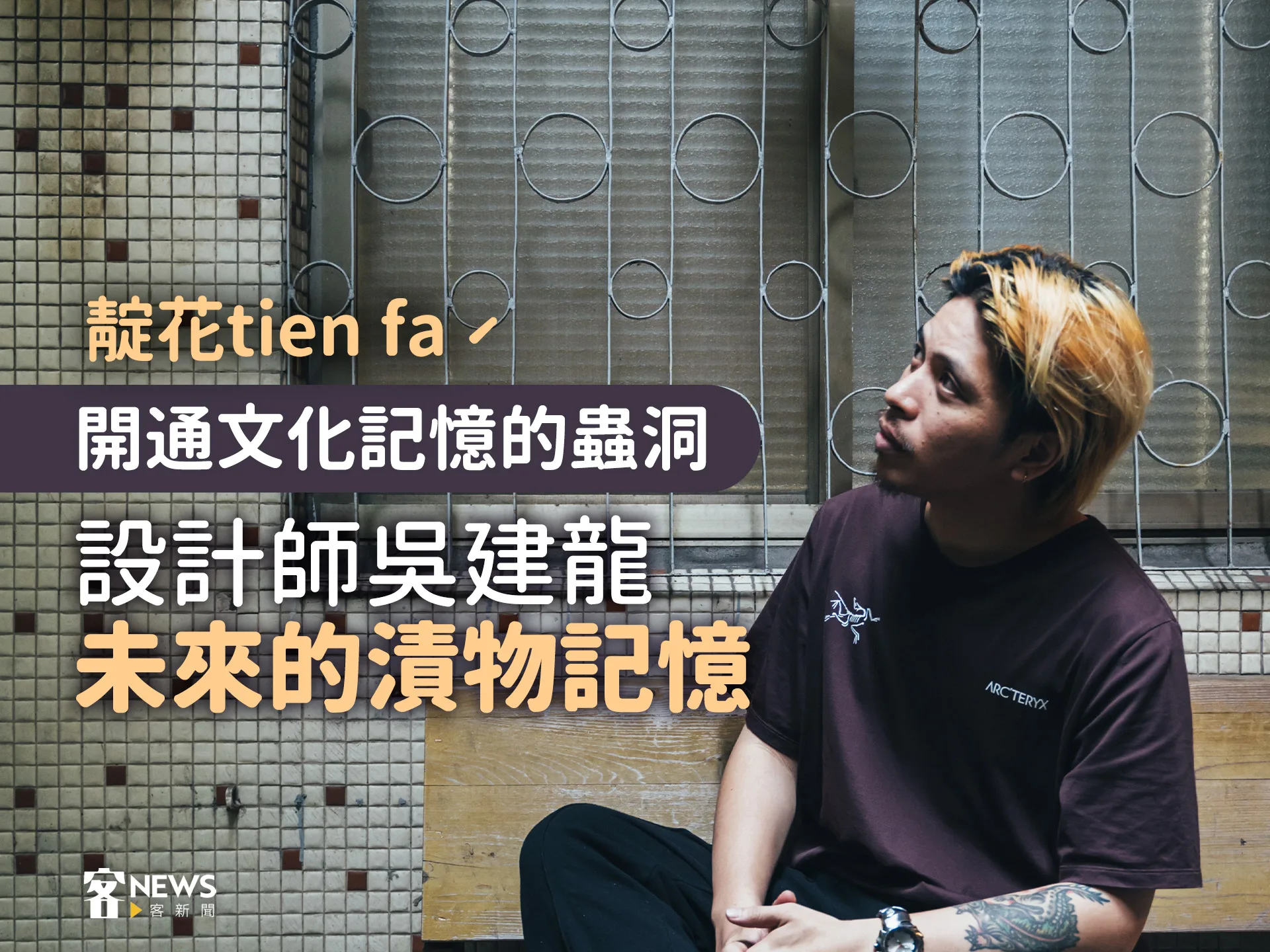文/蕭秀琴
曾任出版社總編輯,現為作家暨譯者,著有《植有武威山茶的小屋》等書籍、翻譯《跟莎士比亞學創作》等。目前住在離台北城約一個小時的小鎮,持續從事文字工作。希望以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完成小說、報導,劇本,翻譯作品。
「細妹仔按靚/就像那一枝花/白白的牙齒/紅紅的嘴唇/目睭會講話」,羅時豐的〈細妹按靚〉是第一次流行歌曲以客語演唱廣受歡迎,也是很多人認識客語歌的開始,甚至是唯一會說的客語形容詞。與專輯同名稱的歌在1992年發行之際,同時收錄台語和客語兩種版本,當時歌手仍然被認為是唱方言的歌星。
時代飛奔,2017年客語抒情歌「細妹恁靚/紅咚咚的面頰/妳就是靚靚的發在我心裡的一蕊花」也是〈細妹恁靚〉,年輕的歌手蕭迦勒以客語歌手的身份出道,理所當然並引以為傲。
客家人用25年的時間提升客家意識先不論成績,有一件事可以非常確定,那就是「細妹恁靚」恁是無庸置疑,如「拐細」(Guai-sii,意即紫蘇)般的紫紅色華麗高貴。
在典籍或客語字典中都找不到為什麼客家人把紫蘇叫成拐細(Guai-sii),到處採集詢問找不到答案,最後才回頭問我媽,「好像聽過Guai-sii恁靚(很美)就像細妹(女孩)一樣,要採下來帶回家。」原來答案就在身邊的意思是如此簡單。
客家人哄小孩叫「拐細人仔」,採一把紫蘇帶回家,好似拐帶美麗的少女。我沒有被人拐走的經驗,因為我阿婆看得很緊時常告誡,倒是被她拐著吃藥的回憶很多,如今想來卻非常甜美,因為吃完藥可以得到一顆糖,糖果吃完還沒補充時,給一顆隨時都有,在罐子裡的甜梅。
仲春之後,經常用紫蘇炒肉,做配料,醃漬,最期待是醃紫蘇梅。不只是紫蘇梅好吃,而是過程有一種安撫鎮定人心的效果,或者說,所有古老的物候傳統都有一種儀式感。
買回來的梅子在水缸裡泡三天,每天都掀開蓋子看看,小孩子看不出所以然,也不知道為什麼是三天,但等到第三天瀝乾水放到蒸籠裡蒸,一股酸甜氣息隨著水蒸氣飄出,會突然感到三天是值得的等待,好運的話會遇上好天,一顆一顆鋪在竹篩籃上,陰天陰乾有太陽曬乾,陽光下升起醉人氣息,口齒生津。
最後一道程序是梅子放入罐子,煮糖水加入,第三天糖水倒掉,再煮新的糖水加入,再三天同樣的步驟,如此三次,第三次加的是用乾燥過的紫蘇熬糖水,加入密封,等待一年後再來開封。
我媽在小舅媽過世19年後找到一罐紫蘇梅,是在清理舊器物時發現了在牆角下的她,20多年前的漬物該不該把它吃下肚?這種機會人生難得幾回,何況有人喝百年前的葡萄酒,自海底打撈起的香檳超過百年被視為人間佳釀,我舅媽的紫蘇梅帶著沉厚的煙醺口韻有點泥炭味,堪比有煤泥味的威士忌還甘醇。
紫蘇(Perilla frutescens (L.) Britt.)源自春秋戰國楚地語言,蘇通舒,疏散鬱氣才能暢達,色紫故名紫蘇。在臺灣的春末到夏天隨處可見,正逢梅子(Prunus mume)成熟期,紫蘇性辛溫,發汗解表理氣消食,梅子歸肝、胃經,具收斂且有生津效果,正是夏日佐餐增加胃口的好食。